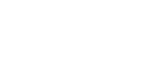小 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自然神论和启蒙运动,以便了解塑造十九世纪神学的三位大师,康德、黑格尔和士来马赫所处的历史背景。面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对宗教的严厉批判和挑战,这三位神学家努力想为人类的宗教刻划一个免受攻击的特定领域,分别从道德 (康德)、知性 (黑格尔) 和直觉 (士来马赫) 重塑基督教,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三位大师的思想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的思想界,先是彼此抗衡,继则融合成为史称十九世纪复原教自由派的神学,最终由第四位德国思想大师立敕尔 (Albrecht Ritschl, 1822 - 1889 AD) 集其大成。”[96] 了解了这三位神学家的思想,就比较容易明白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和它的《圣经》观。
这三位神学巨匠构建的神学领域虽各不相同,但在治学方法和神学前设上却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他们企图在基督教和现代人之间铺设桥梁,使之能接受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们不能对科学至上和唯理主义对基督教的批判作出正面的回应,而是以放弃传统信仰为代价,博取现代人的欢心,在科学和理性无法企及的地方 (如人的道德感和宗教直觉) 为基督教争一席之地。他们建筑桥梁的心志和所付出的努力都是可嘉的。但是,如果基督教这一端的地基已被松动或毁坏,桥梁怎么能建成呢?如果另立地基,桥梁虽然被搭起来了,但恐怕已经不是基督教与现代人之间的桥梁了。第二,他们的神学,高举人的理性,轻忽神的启示,用人的理性取代神的启示,是以人为本的。这种人本的神学有着启蒙主义的深深印记,起码带来两方面的后果。首先,他们的神学已与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大相径庭。比如,救赎观就完全不一样:
在启蒙运动之前,神学家所强调的是,在绝对圣洁、超越的神和罪恶、有限的人之间的决裂,只有神自己用道成肉身这件戏剧化的事件,来填补这条鸿沟。从启蒙运动开始到自由主义的高峰期,神学家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向,用人类所表现出的推理、直觉或道德的能力,来连结神与人;因此很自然地,他们看耶稣只是人类的典范,而不是外来的救主。[97]
其次,他们的神学虽不乏精巧动人、严谨深邃之处,但毕竟只是人的智慧,缺乏属天的亮光。这样,他们的神学就像在黑暗中摸索,产生许多暧昧、矛盾和困惑。 基督教是启示性的的宗教。神若不向渺小、有限的人启示他自己,我们怎么可能认识神呢?神的自我启示已经完备地记录在《圣经》中。人内在的道德律或绝对依靠感是神的普遍启示的内容之一,可以作为神存在的一种依据,但决不能由此认识神的属性。所以,这三位神学家对神的属性基本上是避而不谈的;甚至,对三一神、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等从《圣经》中归纳出来的、超越人的理性的教义,持怀疑态度。 何况,黑格尔的需要在人里面完成自我认识的“绝对精神”、士来马赫的与人的“绝对依靠感”密不可分的神已有泛神论或万有神在论之嫌了。离弃神启示的真理,纯粹用人的方法重塑基督教信仰,必然走向“人造神”的歧途。
再说,人非神,思想再深刻,也并非无懈可击,逻辑再严谨,也会露出破绽。例如,康德把事物分成可认识的现象和不可认识的本质的二元论,有力地批判了理性至上的世界观。“当康德在一七九一年出版《纯粹理性之批判》一书时,理性时代事实上已走入尾声。”[98] 但是,康德的这种认识论的二元论遭到了严峻的质询。贾诗勒 (Norman L. Geisler) 尖锐地指出:
说“本体不可知”这话是无意义的。因为这断语本身含有对本体的知识。正如艾耶 (A. J. Ayer) 说的,“除非康德自己能成功地跨过那些人类知识到达的界限,否则他怎能说出那些界限在哪儿?”或如维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所说,“为了给思想划一条界限,我们应该在这界限的两边作思考。”简言之,除非我们的知识已经到达本体,不然就无法说我们的知识不能达到本体。绝对不可知论是自相矛盾的。……若我们真的只能知道现象 (我见之事物) 而不是本体 (物自身),我们如何能知道两者的区别?为了分辨现象与本体,人必须知道本体是什么,不然他就没有理由去认定这些那些是表象而不是本体。……本体是可能被认知的,事实上,这也是哲学史上最持久的一项假定。[99]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持乐观态度的自由派神学开始势微。自由派神学的具体观点可能随处境而有所变化,但都植根于但康德、黑格尔、士来马赫等人的治学方法和神学取向。贾诗勒是这样综述自由派神学的《圣经》观的:
自由派对《圣经》的观点是,《圣经》并非神的道,它只不过包含了神的道。在《圣经》中,除
了有神的真理外,还掺杂许多科学和神学的错误,必须藉着理性加以铲除,且设法与“基督的灵”相吻合。因此,对《圣经》予以高等批判不但受欢迎,而且对于发现《圣经》中什么是属实的也愈显重要。自由派除拒绝许多《圣经》的教训外,它还是一种反超然主义,驳斥《圣经》中的神迹。《圣经》基本上是一本易于犯错误之人的作品,虽然在道德与宗教的真理上也包含了由“启示”而来的洞察力。[100]
显然,自由派神学的《圣经》观是承接康德等人的遗风,把科学、理性置于神的启示 -- 《圣经》之上,其观点常常是相互矛盾的。比如说,他们否定《圣经》所记载的神迹的真实性。有神就会有神迹。相信神却否定神迹,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而且,他们企图化解神迹的说法也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自由派神学家爱德华斯 (David Edwards) 在与福音派神学家斯托得 (John Stott) 的对话中,是这样化解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时所彰显的神迹的:
这一连串不合科学的故事是由摩西的杖变蛇开始的,接着是摩西的手一伸入袍内,再出来就长了大麻风,如雪一样白。还好,不是每个故事都这样。其他神迹说到尼罗河水变成血、蛙灾、蝇灾,其实还颇符合科学事实的,因为尼罗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浑浊如泥,看来有点像血,漫溢两岸,青蛙、苍蝇滋生繁多,那时牛的确会有瘟疫,埃及人也会长疮,蝗虫到处横行,冰雹密云使中午也为之黑暗。这些事是人所知道的。…… 就算这些神迹是摩西所行,我们还是不能当真,也不用相信“水聚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出15: 8),这其实是摩西所写的诗歌。但又有一种说法是“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乾地” (出14: 21),另一个地方说他们通过红海 (出13: 18)。若这个红海其实是埃及边界的一个纸草沼泽,就不难理解埃及派去追希伯来人的马车会陷在其中不能自拔了。这种合乎自然的解释也能用来解释《圣经》的其他神迹: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可能是西奈半岛的火山景象;有报道说,有些水加一小片木头就可以喝;吗哪几乎可以确定是圣柳植物被一种虫子蜇了后所分泌的东西;至于鹌鹑,那是一种候鸟,飞到没有力气的时候,要抓它们并不难;沙漠中有些泉水为薄薄的石头所掩盖,只要打破这个石头,也就有水了。我不认为我们不把这些当作神迹而只视为普通的现象,就表示我们“不信”。因为《出埃及记》最大的神迹是,埃及的追兵竟然奈何不了他们,大自然又提供必要的帮助,以致他们能渐渐形成神慈爱计划中独特的器皿。[101]
在这一大段文字中,爱德华斯对《圣经》记载的神迹的“化解”是如此地牵强,以致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出自一位严肃的神学家之手。对他的“化解”,笔者将不再着墨,相信读者自有评说。但这使笔者想起一个听来的故事:
一群人到圣地访问,导游把他们带到一片水域,水只没过脚面。
导游:“这就是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时所经过的‘红海’。水就这么浅,风一吹,地就露出
来了。所以,以色列人过红海根本不是神迹!”
访问者 (沉思片刻,顿有所悟):“啊!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确是一个神迹!”
导游:“什么?!我不是刚刚告诉你们,当年的水面就这么浅,你听明白了吗?”
访问者:“我听明白了。但我不明白的是:这么浅的水,居然‘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
人下海的法老全军,连一也没有剩下’(出14: 27 - 28)?”
导游:“……”
爱德华斯这段话的结尾,虽前后矛盾,却是画龙点睛之笔。他告诉读者,他之所以不信这些神迹,是因为它们是“不合科学的故事”;但他仍然相信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迹,因为埃及人竟奈何他们不得!此话令人费解。如果埃及人奈何不得以色列人是由于大自然提供的一系列纯属偶然的帮助,就只能说以色列人碰巧赶上了好运,那就无神迹可言;如果这一连串的非常事件确实是神刻意的作为,就是神迹。那么,为什么爱氏又要煞费苦心地抹煞它们呢?笔者以为,爱氏说“我不认为我们不把这些当作神迹而只视为普通现象,就表示我们‘不信’”,不是“此地无银”,而可能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既想持守基督教信仰,唯恐基督徒批评他“不信 (神)”,又想讨好世俗的“科学至上”的思想,生怕别人指责他“不合科学”;他本想在二者之间搭一座桥,不料被夹在其间动弹不得,进退维谷,捉襟见肘。如果自由派继续轻忽《圣经》,坚持置人的理性于神的启示之上,不惜扬弃《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去迎合世俗的思潮,那么,他们要不最终变成不信派,要不就将永远在矛盾、痛苦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