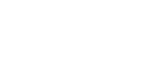“《圣经》原稿无误”的根据和意义
对于“《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通常会受到两方面的质疑。第一方面的质疑是,既然《圣经》的原稿已不复存在,人们怎么能笃定它是“无误”的呢:
我们怎样证明那现今已不复存在的“原稿”是没有错误的?…… 为什么历代以来,纵使没有人曾亲眼见过原稿,却有那么多人坚信这些原稿是可靠无谬的?既然世界上没有人拥有这些原稿,现今的人怎能确定它们是值得信赖的?常识不是告诉我们,对于自己不拥有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切勿妄加评论吗?我们在说这些“原稿”是无误的之前,岂不应该先详细审查它的性质和特点吗?[1]
第二方面的质疑是,既然《圣经》的原稿已经找不到了,强调它没有错误对今天的信徒有什么现实意义呢?甚至有学者认为,坚持原稿无误是不敢正视现今的抄本和译本有错误的“鸵鸟政策”:
“《圣经》(原稿) 无误”的论点,其实正好宣判我们所读的《圣经》,不论是译本或抄本,都是有错误的;所有用以维护《圣经》原稿必须无误的理由,反过来都成为批判我们手上任何《圣经》版本的根据。一份不存在的“无误原稿”,也许可以维系一套神学系统的逻辑完整,然而对于每天读着“有误《圣经》”的信徒来说,这立场有甚么意义和价值呢?正因为这缘故,我们探讨有关启示 、真理和《圣经》等神学教义时,实在不容苟安于“《圣经》无误”这避风港里。[2]
第一方面的质疑是关于“《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的根据,第二方面的质疑则涉及“《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的意义。现逐一予以回应。
对于物质界的事物,人们必须首先运用理性对它们仔细研究、考察后,才能确定它们真确与否。但是,对于属灵的事物、对于有关神的事情,人们则需仰赖神的启示,因为人的理性无法完全了解属灵的事 (林前2: 14 - 15)。《圣经》原稿无误,首先是基于神的启示:《圣经》是神默示的 (详见第三章)。当使徒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后3: 16) 时,他的意思是说:《圣经》的所有书卷的写作,包括作者和作品,都是在圣灵的完全控制下完成的。所以,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指《圣经》的原稿,而不是指《圣经》的抄本或译本,也就是说,“《圣经》无误”是指《圣经》的原稿,而不是指 《圣经》的抄本或译本。事实上,《圣经》的抄本或译本也确实发现有误抄或误译的地方,并不是“无误 ”的。其次,《圣经》原稿无误也是有事实根据的。“成千上万的抄本中,只出现少许的差异”,[3] 是《圣经》原稿无误的证据之一。再者,虽然当今没有人见过《圣经》的原稿,但是,曾经有人见过《圣经》的原稿: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说我们没有看过“原稿”,怎能相信默示呢?其实不然,因为有些人是见过“原稿”的,例如公元二百年的特土良 (Tertullian) 说,在他当时的教会里仍有不少人见过新约书卷的原稿。今天我们仍有少部分特土良时代的新约,甚至有一块比他早七十年的小片断呢!而且,当时通用的抄本时常与这种原稿校对,同时,现存的抄本大都是与原稿极相近的,为此,我再强调:新约的抄本都是有优良与可靠的本质的。《圣经》的确是神的灵所写作的,有属天的信息赐给我们,来喂养我们的灵命。[4]
应该说,关于“《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主要是根据神的启示,并没有完全的证据。但不必为此苦恼,因为没有任何基督教的教义有完全的证据的支持。比如,并没有完全的证据支持神的存在。“神是个灵”(约4: 24) 这个事实使人无法找到完全的证据证明神的存在;完全的证据要求人们能够看见神,以致可以检验神的特点和性质。但是,大家仍相信神的存在,因为虽没有完全的证据,除了“信心”的因素外,还有充分的证据支持神的存在。有关三一神的真理,也是如此。是否神在《圣经》中的宣称,就可以成为“《圣经》原稿无误”教义的坚实依据呢?答案是肯定的。正如贝查 (Richard P. Belcher) 所指出的,“基督徒要接受《圣经》为最有权威的‘充足证据’”:
教义性的真理不是用完全的证据来证明的。三位一体的完全证据在那里?我们认识三位一体是基于《圣经》的充足证据。创造论的完全证据在哪里?道成肉身的完全证据在哪里?有关基督的死 、复活和神迹的完全证据在哪里?完全证据要求我们审查所有的第一手的资料,这点我们是办不到的。然而,如果正如有关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接受以《圣经》中的充足证据为基础的教义。
我以为我们既然接受以充足的证据作为衡量教义的根据,而不是根据完全的证据,那么,关乎《圣经》本身及其性质、特点的教义问题,我们也必须以神的话语为充足证据。如果有人对基督教的其他教义不要求找寻完全证据,却偏要为《圣经》的性质问题寻求完全证据,他便是自相矛盾了。如果我们否认《圣经》说明自身性质的权威,就必须怀疑它是否能作为其他教义根据的权威。
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拥有那些原稿,而在于 《圣经》对其本身怎样说。[5]
既然《圣经》的原稿已经失散,现在强调它“无误”还有现实意义吗?有意义,而且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圣经》的原稿是无误的,通过经文鉴别学的工作,人们才能从各个抄本中鉴定出最接近原稿的经文,才能知道这些经文所包含的真理。如果 《圣经》的原稿是有错误的,即使经文鉴别学完美无瑕地把原稿的经文重新构建起来,所得到的经文仍是不准确的,因为原稿本身就是有错误的。这样,人们仍不能确定已经得到了真理。所以,如果不坚持《圣经》的原稿是无误的,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文鉴别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至于“‘《圣经》原稿无误’的论点,其实正好宣判我们所读的《圣经》,不论是译本或抄本,都是有错误的”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坚持“《圣经》的原稿无误”并不能导出“现今的《圣经》版本有错误”的结论,两者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没有一个现代人看过无误的《圣经》原稿也许是对的,然而,没有一个人看过有误的《圣经》也是一个事实。”[6] 现今的《圣经》的版本,虽然在抄写或翻译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少许失误,但很容易从不同版本的对比中得到纠正 (详见下文)。何况,主张《圣经》有错误的人也并不是指这一类在翻译或抄写中的错误,而是认为《圣经》在科学、历史上有错误,认为《圣经》在许多神学观点上前后不一致、彼此冲突,等等。然而,他们所提出的《圣经》的这些错误,到现在并没有被证实。所以,“‘《圣经》原稿无误’的论点,其实正好宣判我们所读的《圣经》,都是有错误的”的说法,既不合逻辑,又与事实相悖。
坚持“《圣经》原稿无误”是苟安于“避风港”、是“鸵鸟政策”吗?当然不是。这种说法离题就更远了。“《圣经》原稿无误”是基于《圣经》的原稿是“神所默示的”的宣称,是从初期教会到现在,基督教会的一贯立场,与“避风港”根本拉不上关系。如前文所述,启蒙运动以降,《圣经》遭到自由派神学、高等批判学的猛烈攻击、无情宰割,大有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然而,《圣经》,神的永活的道,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虽然坚持《圣经》有错误的人耗费了无可计量的心血,至今他们仍拿不出《圣经》有错误的确凿证据。他们对《圣经》的批判也从锋芒毕露、旗帜鲜明变成躲躲闪闪、吞吞吐吐。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圣经》无误”的人,有什么“风”可避、有什么“苟安”可求呢?
再者,批判学者认为《圣经》有错误,并不是指《圣经》的抄本或译本有错误,而是指《圣经》的原稿有错误。可是,他们同样没有见过《圣经》的原稿。卡尔亨利 (Carl F. H. Henry) 指出:“批判学者们也拿不出一本他们一直假定存在的错误原典。在这两种情形下,原典的正、误都是从资料和教义推论而来的。所谓有误的原典和无误原典,都同样尚未出现。”[7] 既然批判学者凭一己的神学立场可以声称自己没有见过的《圣经》的原稿有错误,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对基于《圣经》自我宣称的“《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如此冷嘲热讽、耿耿于怀呢?既然批判学者不断声称《圣经》的原稿有错误,广大基督徒就有必要一直高举“《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坚持“《圣经》原稿无误”,哪里是“苟安于避风港”呀,这分明是在针锋相对地捍卫《圣经》的神圣权威。
神为什么没有使《圣经》的原稿保留下来?没有人知道。有学者推测,《圣经》的原稿没有保留下来,可能因为人有崇拜遗物的倾向,《圣经》已记载了这样的先例。出埃及、进迦南的路途中,以色列人又发怨言,于是耶和华神使火蛇进到他们中间。经摩西代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民21: 8 - 9)。但是,被保留下来的这条铜蛇,却被以色列人当作偶像崇拜,直到犹大王希西家领导犹大国复兴时,才将这铜蛇和其他偶像一起除掉:“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王下18: 3 - 4)。如果《圣经》的原稿被保留下来,人们会不会也像对铜蛇那样,向它敬拜、烧香呢?[8] 这种推测不无道理。不过推测毕竟只是推测。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由于《圣经》抄本的准确性和经文鉴别学的巨大成就 (见下文),学者们已构建出非常接近原稿的《圣经》版本。正如贝查所说:“纵然我们现今没有一本毫无错误的原稿,我们仍有一本可靠、足以应付各样实践需要的《圣经》,可供我们深入研读,和藉此制订教义。”[9] 一九七八年的签署的《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第十条(The Chicago Statement of Biblical Inerrancy, 1978, Article X)也宣称:“我们确认,‘默示’,严格说来,仅是针对《圣经》原稿说的,在神的护理保守下,从现存许多抄本可相当准确地确定原稿。我们并确认,《圣经》的抄本与译本,如忠实表达原稿,即是神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