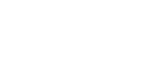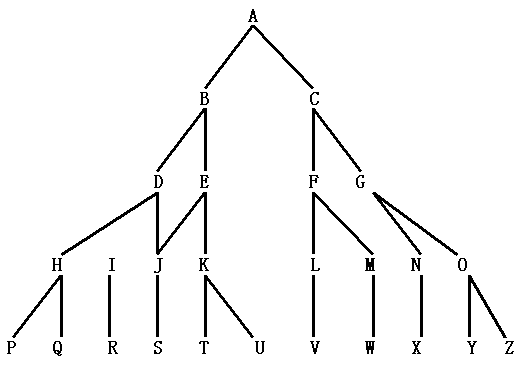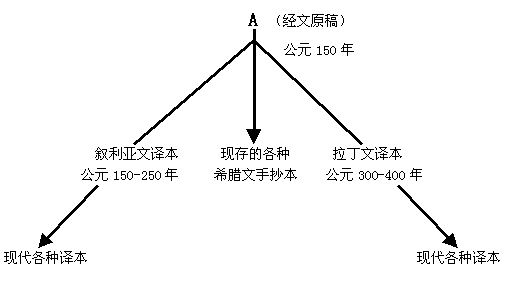第四章 圣经的可靠性
|
第四章 圣经的可靠性 |
||||||||||||||||||||||||||||||||||||||||||||||||||||||||||||||||||||||||||||||||||||||||||||||||||||||||||||||||||||||||||
|
第一部分 历史文献印证圣经的可靠性 4A.圣经的可靠性与可信性 1B.序言 这里我们要证实的乃是圣经在历史上的可靠性,而不是讨论圣经是否神的默示。 在查证圣经在历史上的可靠性时,我们必须采用考证一般历史文献时所用相同的衡量标准,这样才算公平。 森德斯(C.Sanders)在《英国文学史研究简介》(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in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一书中曾列举三种基本考验及编纂史料的原则:参考文献的测验(Bibliographical Test)、文内证据的测验(Internal Evidence Test)、及文外证据的测验(External Evidence Test)。 2B.新约圣经之可靠性──按其参考文献考验方式来衡量 所谓参考文献的测验乃是检察所留传下来的文件,看其中章节及文字的真伪。换句话说,在缺乏原本的情况下,抄本的可靠性如何?抄本的数目共有多少?又抄本与原本之间共相隔多少时间?34/26 1C.学者印证新约的可靠性 美国圣经校订委员会委员艾博特(Ezra Abbot)在其《批评文字》(Critical Essays)一书中论道:“经文具有各种不同的抄本,其数目之多令无心的读者咋舌,但我们要记这个数字通常只是一般不信基督教之作家们所提供的数字,说总计‘共有十五万种!’数目如此之大,这样看来岂不证明新约圣经确实不甚可靠,这会不会影响我们信仰的根基呢? “其实不会,根据诺顿(Norton)先生的看法,在这15万种希腊新约抄本中,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不可靠的,可以将它删去。因为显然都是膺品,很少受到圣经权威人士的支持,也没有经文批评家会正式接受它们。这样一来,我们就只余下7500种待鉴的版本。然而再经细察之后,我们又发现,在这7500种抄本中,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抄本差异都是不足影响版本内容的,他们只涉及拼字法、字法结构、字句排列次序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对研究经文内容实无伤大雅。 “至于那些只注重辞句表达的方式,却不重经文含意的版本,我们亦可略去。这样一来,真正余下来值得考证的抄本只有四百种左右。但其中涉及真正不同经文含意的抄本并不太多,有些抄本在经文字句的增减上稍有出入,但能真正引起学者的好奇与兴趣的并不多,只有极少数的版本是真正算是有问题的。但如今圣经批判学家们人多势众,评审、鉴定抄本的工具充足,因此这些抄本中所谓较严重的问题都得以一一解决,被经学家们断定为真的经文均是相当可靠的。这与鉴定古代的文学作品有何其大的差别,许多文学古著我们不但不能完全肯定它的字句,连对那些用来解释原文的文字其可靠性,我们也都会有所怀疑,然而圣经内容的鉴定却没有这类的困难!”30/4 沙夫(Philip Schaff)在《希腊新约圣经版与今日英文版之比较》(Comparison to the Greek Testament and the English Version)中表示,在所有15万种抄本中,只有400种版本其中经文原意可能是有疑问的经文,然而在这四百本中仍只有五十种是真正值得待鉴的。但沙夫强调说,尽管有版本上的差异,它们“却不足以影响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及信徒的职守,因为有他处的经文,甚至他处已被证实的经文以及整本圣经中连贯的思想都能印证这些基要的教训,全书不会只因一两处不能确定的经文影响而动摇。”42/117 华费尔(Benjamin Warfield)在《新约文句批判》(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New Testament)之序在引用艾博特(Fzra Abbot)对十五万种抄本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差异都是不值得考证的看法说:“……。他们为数虽众,却极少受经文批评家的支持,这百分之九十五的差异实微不足道,无论采不采用,对经文本身之意义实不生影响。”54/14 盖司乐与尼克(Norman Geisler and Willian Nix)对取舍抄本中之差异有如下的建议:“若说从新约圣经抄本中,我们能找出20万处文稿的差异来,这种说法则未免太过含糊一些,事实上只能说新约中约有一万处左右的差异。因为如果一个错字在三千本抄本中出现,我们仍算是三千个差异。”14/361 何德(Fenton John Anthony Hort)曾毕生研究圣经抄本,因此一直被视为经卷考证的权威,他说:“圣经中有八分之七左右的部分,被专家们认为是可信的,至于其余的八分之一在经文批评学中看来,只限于文句排列的先后次序的不同,有些太过琐碎根本无足轻重。 “如果这个取舍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差异的范围就可大为缩减。如果我们手边有二、三种不同的抄本,而我们已下定决心,若非找到绝对的证据,将不轻易武断地决定经文的对错,然后我们姑且再略去抄本拼字法不同的差异不论,那么新约圣经中的字句真正值得我们怀疑的,大约只占全部新约全书的十六分之一。若以此计算,那么我们就知道一般所谓的差异都是极琐碎的,真正值得研讨的只占差异总数的极小部分,甚至不超出全部的千分之一。”22/2 盖司乐和尼克(Geisler and Nix)对何德的看法有如下的补充说:“其实只有八分之一的差异是真正算是有份量的,其他仅仅是拼字法和文体上的出入。就整体而论,只有十六分之一的差异是重要的,或算是为‘较严重的差异’。若用数字来统计,那么新约圣经中有百分之八十八点三三(88.33%)的部分都是纯正无误的。”14/365 华费尔(B.Warfield)大胆宣布说:“新约圣经留传至我们手中时,其中内容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无误的,即使是最差的版本亦不例外,我们可引用班德赖(Richard Bently)的话来证明:‘圣经的经文绝对真实、准确……其中的信条与道德教训均被完整保存着──无论你如何挑选版本,即使故意挑选最差的版本,其中内容依然不会改变’。”54/14;55/165 沙夫(Philip Schaff)分别引用崔格拉及史瑞挪(Tregelles and Scrivener)的话说: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圣经版本,又有这么多的考证工具,因此我们不必用凭空揣摩的方式,将版本中差误的部分除去。”摘自崔格拉所编之《希腊新约圣经一序言》(Greek New Testament,Prolegormena,P.X) 史瑞挪(Scrivener)说: “虽然抄本数目太多,有时使真正学圣经的学生深感疑难、困惑,但这却也能同时引导他从这些差异中更进一步地体会出圣经的完整性。如果伊果齐鲁(Eschylus)的读者能同时拥有这许多伊氏作品的版本资料,使他们在欣赏伊氏升华性的诗篇时不必伤透脑力,费尽耐性,而能寻得诗句的准确性,他们将不知会有多喜乐呢!”42/182 布如斯(F.F.Bruce)在《经书与羊皮古卷》(The Books and the Parchments)一书中写道:“万一没有其他客观的文字证据能用来修正圣经抄本中显然的错误,经文批判家则须靠臆测的方式来修正此错误,但要使用臆测的方式则需要高度的律已精神,它不但要能说明修正时所选用的字是绝对正确的,它也必须能说明版本中原有的错误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换句话说,这种修正不但对‘原文来说是合理的’,在运用到‘不同抄本上时也一样合理’。然而各新约版本中需要使用这种臆测修正法来修改经文错误之处者,却几乎可以说没有。证明经文之准确性的证据为数甚众,可谓俯拾皆是。从成千的证据当中,至少总有某处的某一版本,能将真正原来的经文保存下来。”6/179,180 甘扬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乃当今最伟大的新约文字批评家,他一再强调经文的错误绝对不足影响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他说: “我最后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并不建立在一句会引起争论的经文上。但如果我们一味只提及这些经文的错误和文句上的差异,必然使人对圣经的内容及文字产生怀疑,以为圣经是经不起审定的。 “我们强调圣经内容绝对可信,实非言过其实,特别新约圣经其经文内容尤其可靠。它除有多种抄本之外,又有早期的新约译本及教会早期作品中所引用的新约文字,可以用作勘校的参考资料。任何一处有问题的经节,都可以从这些参考资料中找出其正确的愿意来,世界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却没有这样的优点。 “世间学者对一些重要的希腊及罗马作家们,诸如:沙孚克理斯(Sophocles,古希腊悲剧作家)、苏西载得士(Thucydidus,希腊史学家)、西赛禄(Cicero,罗马政治家及演说家)、魏吉尔(Virgil,罗马诗人)这些人所遗留下来的作品甚觉满意,对这些作品的内容正确与否也从不怀疑。但这些作品只有少数抄本流传于世,至于新约圣经却有成百成千的抄本留存于世。”25/23 华费尔(Benjamin Warfield)说: “我们若采目前新约圣经的经文,与古时的新约抄本相比,我们就……不得不为两者相近似的程度感到惊异。新约圣经是经人细心抄写才留传下来的,抄写的人之所以细心,完全是出于他们对上帝的话敬爱的缘故。这也是上帝格外的恩赐,使他的教会能在每个时代中保存一部全部无误的经书。若与其他世俗的古典文学相比较,所留传下来被世人一直使用的新约圣经远较任何古书数量为众。不仅如此,许多早期信徒所留传下来的其他著作及见证中,足供我们鉴定、修正新约版本中为数稀少的不准确部分,这些优点都远非其他古典作品所能及。”54/12f。 英语重订标准译本圣经(Revised Standard Version)的编者说: “任何一位生于1946年的细心读者都会同意,基督教的信仰不会因出版重订标准译本的圣经受影响。他所信仰的内容正与1881年或1901年的信徒所信的完全相同。理由很简单,圣经在版本上虽有许多差异,但从没有一个差异大得足以让我们将基督教的教条提出加以修改的。”16/42 史垂特(Burnett H.Streeter)相信由于有大量的新约版本流传下来,“经文的可靠性应当是很高的。”46/33 甘扬爵士(Sir F.Kenyon)在《圣经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Bible,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出版)一书中又说:“经过多年来苦苦追寻经卷的底细,经过多年来的研究工作,我们终于印证圣经的准确性,也看出我们手中所拥有的这卷书诚然是可信的,它是上帝真实不变的话语。”26/113 耶鲁大学的鲍罗斯(Millar Burrows)在《石版的意义》(What Mean These Stones?Meridian Books,1956年出版)中写道:“再一次将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与古代纸草经卷比较的结果,能使我们对经文流传的正确性又增添不少信心。“68/52 鲍罗斯又说,经文“在流传时所保存的准确性实令人钦佩,人对其中所含之教训实不应再起任何的疑惑。”68/52 福斯(Howard Vos)在《我应否相信圣经》(Can I Trust My Bible,Moody Press,1963年出版)一书中宣称说:“单由考证文学证据的立场来评断,新约圣经的可靠性就已远较其他古书来得有力。”79/176 2C.抄本的数量印证圣经的可靠性 罗拔逊(A.T.Robertson)是新约希腊文最完整的文法编著家,他写道:“拉丁文通俗译本圣经(Latin Vulgate)共有八千种抄本,其他更早期的抄本约有一千本左右。再加上希腊文四千本手抄本(普林斯敦大学神学教授莫志杰Bruse Metzger则认为我们至今已找出五千本的手抄本。33/36),另有一万三千本不全的新约手抄本。除此之外,由早期的基督徒作品中,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作者所引用的经文。”39/29 莫志杰(Bruce Metzger)说: “在这五千份希腊手抄本中……其中包括全部或部分的新约经文……”33/36 孟沃华(John Warwick Montgomery)说:“如果我们对新约圣经中的各书卷持怀疑的态度,也就等于贬低其他古典巨著的地位,因古代的文献中没有一部比新约圣经更可靠了。”34/29 甘扬爵士(Sir.Frederic G.Kenyon)是大英博物馆馆长兼图书馆馆长,也是一般学术界中首屈一指的圣经抄本权威人士。他说:“……除了数目庞多之外,新约圣经的手抄本与其他的古典作品还有一个迥异之处,这点对新约的考证工作十分有利。在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部文献写成的时间与其最早存在的手抄本相隔的时间,象新约圣经这样短的。新约各书卷是在公元第一世纪末期写成,但如今所存最早的手抄本则多来自第四世纪──其间只相隔250年至300年。 “ 这段时间听来似乎很长,但与多数古典作品相较则显得不然。我们相信现在我们已经收全古希腊作家沙孚克理斯(Sophocles)的七部悲剧作品,这些手抄本也是今日被用来编纂沙氏基本作品的蓝本,但都是在这位伟大的诗人死后一千四百年才抄写的。“24/4 甘扬爵士(Kenyon)在另一部《圣经与考古学》(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中又继续说:“由于新约写成的日期距离现存最早的手抄本,其相隔时间过于短暂,可见怀疑抄本与原著间会有出入这一点已被人视为毫无根据,而新约圣经中各卷书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也终于被学者们所确定。”56/288 3C.新约手抄本与其他古典文学著者与其作品的比较 近代伟大的英国学者布如斯(F.F.Bruce)在《新约文献》(The New Testment Document)一书中,曾极生动地描述新约圣经与其他古典文学的不同:“当我们把新约圣经的抄本与其他古代具有历史性的文学著作相比时,我们就更可以欣赏新约抄本资料是何其丰富!凯撒的‘高卢之战’(Gallic War)约写于公元前58年与50年间,但如今所存抄本无几,其中只有九十一本能算是较好的版本,而最早的抄本约在凯撒去世几百年后方才写成。而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后17年)曾著有罗马历史凡142册,却只有35册流传下来,手抄本的数目不超过二十本,其中仅一本包括第三至第六章的一片段史记,是在公元第四世纪写成,算是最早的一份抄本。罗马史学家塔西图(Tacitus)约在公元100年左右写成十四本史书,但只有四册半存留下来,塔西图另著有十六本年鉴,有十本被完整地保留,另二本只是部分的抄本。而如今我们所有塔西图的作品都是根据这两本不全的手抄本写成,一本来自第九世纪,另一本则来自十一世纪。 “今日我们所收集的罗马大将阿古可乐(Agricolo)的作品《论修辞学之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则来自第十世纪的一份手抄本。公元前460至400年间的雅典史学家苏西戴得士(Thucydides)所著的史记,则来自八本在公元900年完成的手抄本及一些与早期基督徒时代同期的纸草抄本。另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8至428年)的作品之来源亦如上述。然而却没有一位古典文学的学者会怀疑希罗多和苏西戴得士的作品,仅管这些抄本的时代与原著写成的时间差上1300年是时间。”7/16,17 何尔(F.W.Hall)在Oxford,Clarenden Press,1913年古典文学之良友丛书(Companion to Classical Text)中著有“古典文学作者与其作品之手抄本的权威性”(MS Authorities for the Text of the Chief Classical Writers),我们试将其中资料抄录如下:
|
||||||||||||||||||||||||||||||||||||||||||||||||||||||||||||||||||||||||||||||||||||||||||||||||||||||||||||||||||||||||||
鉴定年代的方法:以下数种因素可以确定手抄本写成的年代:14/242246
赖兰抄本(John Ryland MMs)是最早的一份新约圣经手抄本,约在公元130年左右写成,现存于英国曼彻斯特的赖兰图书馆:“因为它发现的日期甚早,所发现的地点(埃及)距离一般新约书卷写成的地点小亚细亚一带甚远,因此这一部分的约翰福音手抄本可以印证该福音约在第一世纪末期时写成的。”32/268 莫志杰(Bruce Metzger)谈及如今已经止息的圣经评论说:“如果这一小部分的经卷能在半世纪前就被发现,那么由托宾根教席教授波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Tubingen Professor)所兴起强辩第四部福音书是在公元160年才写成的说法,早就不攻自破了。”33/39 彻斯贝弟纸草抄本(Chester Beatty Papyri)约在公元200年左右写成,现存在都柏林的贝第博物馆,其中一部分经卷属美国密西根大学所有。这部藏书包括纸草写成的经卷,其中三卷包含大部分的新约经文。6/182 甘扬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在《圣经与现代学术研究》(The Bible and Modern Scholarship)一书中说:“这卷书的发现是继西乃山经卷后最重要的另一项发现。它大大缩短最早手抄本与新约书卷传统所定写成日期间的距离,更证实圣经的可靠性。没有任何古典文献有如此多及如此早期的见证,来印证其原著的可靠性。凡是心无成见的学者都会承认这些流传给我们的经卷是可靠的。”23/20 宝地母纸草经卷手抄本(Bodmer Paparus Ⅱ)约在公元150年至200年间写成,现存于世界文学宝地母图书馆中,经卷中主要包括的是约翰福音。 莫杰志(Bruce Metzger)说: “这份手抄本是‘自彻斯贝第纸草手卷后的另一项最重要的发现……”33/39,40 维也那国立图书馆纸草经卷收集部负责人汉格(Herbert HUNGER),曾在1960年第四卷的“奥地利科学会月刊”中第12033页上著有“宝地母纸草经卷的年代鉴”一文(Zur Datierung des Papyrus BodmerⅡ),他认为应将宝地母纸草经卷写成的日期订早66年,若非是第二世纪初叶时期写成,则应在第二世纪的中叶所完成的。参看其论文。33/39,40 Diatessaron乃四福音合参之意。希腊文dia Tessaron一字则是“四合的”意思。6/195,这是指塔弟安(Tatian)在公元160年所完成的同时叙述耶稣生平的四福音书而言。早期教父优西比渥(Eusebius)在《教会历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IV,29Loeb ed.,1,397)中写道:“……他们的领袖塔弟安(Tatian)写成四福音的合并文集,命名THE DIATESSARON(四部合谐之义),此书至今尚在……“塔弟安乃亚述的基督徒,相传是抄写四福音的第一人,如今仅有一小部分手抄卷存留下来。14/318-319 西乃山抄本(Codex Sinaiticus)约在公元350年写成,现存于大英博物馆中。12/579这份手抄经卷除缺马可福音十六章9-20节及约翰福音七章53至八章11节外,几乎包括新约圣经的全部及旧约圣经的大部分。是在1844年在西乃山的修道院中,为德国学者戴辛多夫(Tischendorf)所发现,后由该修道院于1859年呈赠俄国沙皇,至1933年圣诞节时,复由英国政府及人民合资以十万英磅向苏联买下来。4/183 亚历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在公元400年间写成,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大英百科全书相信此卷是在埃及以希腊文写成,几乎包括整本圣经内容。 梵帝冈抄本(Codex Vaticanus)约在公元325至350年间写成,现存于梵帝冈图书馆内,抄本包括全本圣经。莫志杰(Bruce Metzger)认为这是最有价值的希腊手抄本。 以法连抄本(Codex Ephraemi)写于公元400年,现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中。大英百科全书称它“约在第五世纪时问世,其中所提供的证据,使新约圣经的部分经文得以确立。”12/579;6/183 此抄本中除缺帖撒罗尼迦后书与约翰二书外,整本圣经中各书均包括在内,这是一份羊皮卷,其上曾题过字,后被刮去,重新用来书写经文。 贝撒抄本(Codex Bezae)约在公元450余年时写成,现存于英国剑桥图书馆中,包含同时用希腊文及拉丁文写成的四福音及使徒行传。 华盛顿抄本,又称福利康奈抄本(Codex Washingtonensis or Ffreericanus)约在公元450至550年间写成,所包括的四福音,乃以下列次序写成: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及马可福音。 布如斯(F.F.Bruce)说: “古典作品中没有一部象新约经卷一样,能拥有这么丰富的证据。”6/178 葛林理(H.Harold Greenlee)也说: “……新约圣经的手抄本数目远较一切古典作品的手抄文为众。再说,现存最早的新约手抄本,其抄成的时期与新约圣经首先写成的时间相隔甚短,这也是一般古典文献所不能及的。”19/15 何德(F.J.A.Hort)说得不错:“新约圣经的准确性完全可由各种客观的证据得到印证,这些证据种类繁多,一般古典作品实难望其项背。”22/561 何德曾花费二十八年的时间研究新约圣经的文字,难怪邵德实(Alexander Sautes)称何氏与魏思考(Brooke F.Westcott)合作对新约圣经的简介,实乃“任何国家均无法超越的一项颠峰成就。”44/103 葛林理(H.H.Greenlee)在《新约版本校勘简介》(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中谈到新约书卷写成的日期与其手抄本相继完成的日期,其间隔的时间时,他说:“大多数的希腊古典作者,其最早的手抄本多半是在作者死后一千年之后才有的,罗马作者们手抄本间隔原著的时间则较短,最短的是魏吉尔(Virgil,罗马诗人),只隔三百年的时间。然而新约圣经,其中最重要的二份手抄本都是在新约圣经原著完稿后不及三百年就都已完成了,甚至某些片段抄本完成的时间与新约原著完成的时间相隔尚不及一百年。”19/16 葛林理又说:“古典文学作品手抄本与原著时间相隔甚远,手抄本的数量不多,但学者们从来不怀疑它们的价值,这样看来新约圣经的可靠性不是比它们更为显而易见么?”19/16 莫志杰在《新约经文》(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中曾叙述两者的比较:“多数的古典文献都是藉着不十分可靠的线路流传给我们的。比方说,彼得克特(Velleius Paterculus)所著《简略的罗马史》之第一版只靠一份不全的原稿编成──然而到了十七世纪,当这份文稿最后一次在阿姆巴克(Amerbach)由雷纳那斯(Beatus Rhenanus)抄录后又不幸失落。” “再用塔西图(Tacitus)的《年鉴》为例,头六册资料均根据一份来自第九世纪的手抄本所编成。1870年时,常被早期基督教编者编入教父文集中的‘致底亚格拿塔斯书’(The Epistle to Diagnetus),忽因法国史查斯堡图书馆(Strasbourg)着火而焚毁。与以上资料相比,新约圣经的经文批判家能享用如此丰富的资料,岂不该引以为傲么?”32/34 盖司乐与尼克(Geisler and Nix)比较新约文献与古典作品本文的差异后,这样总结说:“经比较后,仅次于新约圣经,拥有最多参考文献的就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德(Iliad,写于643年),两者均被视为‘圣书’,两者的希腊抄本同时在版本内容上有所改变,同时均受过专家们的批判。新约圣经原包括2万个字句。”14/336 他们又继续说:“伊利亚德则有15600句。新约圣经中有40句(或400个字)是有疑问的,伊利亚德中有764句有疑问。换句话说,伊里亚德中有百分之五的部分有问题,圣经只有百分二点二的部分值得校勘。 印度国定的史诗,Mahabharata其中错误的地方更多,比伊利亚德和奥德赛合起来的25万句中所能找出的错误尚多八倍,其中有百分之十的部分均与原稿内容有关。” 手抄本数目众多另有一个好处,因藉这些抄本我们较易重组原文。 |
||||||||||||||||||||||||||||||||||||||||||||||||||||||||||||||||||||||||||||||||||||||||||||||||||||||||||||||||||||||||||
|
|
||||||||||||||||||||||||||||||||||||||||||||||||||||||||||||||||||||||||||||||||||||||||||||||||||||||||||||||||||||||||||
|
自P至Z的部分开始,我们可以重构成原稿A来。 早期的手抄本可以印证原稿的可靠性,主要“因为古代作品很少在初流传之际立即被译为他国文字的。”19/45 但基督教自创始就是一种向外传的信仰。 “新约圣经最早的译本是由一群传道士用古叙利亚、拉丁及北非文字写成,为向这些外国人传福音,便利他们阅读所准备的。”33/67 以叙利亚及拉丁文写成的新约圣经在公元150年左右开始出现,这与新约本身写成的时间十分相近。 |
||||||||||||||||||||||||||||||||||||||||||||||||||||||||||||||||||||||||||||||||||||||||||||||||||||||||||||||||||||||||||
|
|
||||||||||||||||||||||||||||||||||||||||||||||||||||||||||||||||||||||||||||||||||||||||||||||||||||||||||||||||||||||||||
|
古叙利亚文版本约在第四世纪时所抄成,包括四部福音书在内。但我们要注意,“当时人们称信基督教的闪族人为叙利亚人,这些译本乃是用一种特殊的闪族亚兰语字母写成。”6/193 莫伯索西亚的席亚多(Theodore of Mopsuestia)写到:“它被译为叙利亚的文字。”6/193 叙利亚文通俗译本(Syriac Peshitta)Peshitta字的原意为“简单”,此乃公元150至250年左右所完成的标准译本。自公元400年流传下来的此类译本尚有350份左右。15/317 斐罗圣尼版本(Philoxenian)约在公元后508年时写成,是教会先父波里克为马博主教(Bishop of Mabug)斐罗圣尼(Philoxenas)所译成的新叙利亚文新约圣经。37/49 哈克兰叙利亚文版本(Harkleian Syriac)由哈克地的多马(Thomas of Harkle)于公元616年译成。 巴勒斯坦叙利亚文版本(Palestinan Syriac)一般学者考据此版本是在公元400至450年(第五世纪左右)所译成。33/68-71 古拉丁文版本(Old Latin)在第四至第十三世纪时,一直有人见证说在第三世纪时,有一种“古拉丁文新约版本在北非及欧洲流传……” 非洲古拉丁文版本,又称巴比尼士版本(African Old Latin,or Codex Babbiensis)约在公元400年左右完成。莫志杰(Bruce Metzger)说:“劳依(E.A.Lowe)曾给人看他自第二世纪纸草经卷上抄录下的古文记号。”33/72-74 可比安拉丁文版本(Codex Corbiensis)其中包含四福音书,约在公元400至500年间完成。 委西冷兰拉丁文版本(Codex Vercellensis)约在公元360年写成。 巴拉丁拉丁文版本(Codex palatinus)约在第五世纪时写成。 拉丁文通俗译本(Latin Vulgate)耶柔米乃大马士革城的教区秘书,后成为罗马主教。他曾应主教之命,将新约圣经于公元366年至384年间译成拉丁文。6/201 布如斯(F.F.Bruce)认为第一部埃及文新约圣经很可能是在第三或第四世纪时所译成。15/214,6/214 沙希德版本(Sahidic)于第三世纪初叶开始出现。67/79-80,33/79-80 巴海里克版本(Bahairic)编者克色尔(Rodalphe Kasser)认为该版本是在第四世纪左右所译成的。19/50 中埃及文版本(Middle Egyptian)于第四或第五世纪。 亚美利亚文版本(Armenian)约在公元400多年时,似乎是从君士坦丁堡的一本希腊圣经翻译而来。 乔治亚文版本(Georgian)俄国外高加索人所用的文字 大英百科全书说:“考证经文的学者虽然审查过不同的抄本后,若尚未参考过早期教会学者们的著作,他仍算没有用尽新约圣经的证据。因为早期基督徒的著作经常与一两种抄本的文体有区别。当传统的原文字句遗失后,这些早期教父的作品往往就成了唯一用来查考圣经原始文字的代表资料,尤其如果他的作品能与其他手抄本的文字相符时,这些作品就成了最好的核勘参考文献,经文批判学家们在未参考这些人的作品前,不应任意下断语评论抄本的真伪。”12/579 葛林里(H.Harold Greenlee)说,在早期基督徒的作品中多处引用新约圣经中的经文:“次数极多,即使不用新约抄本,单从这些被引用的经句,拼凑起来,也可重新编出一部新约圣经来。”37/54 莫志杰(Bruce Metzger)论及在一般解经书籍及讲道集中所引用的圣经经句时,也重复以上葛氏的看法说:“是的,被引的经节数目甚多,即使任何其他有关新约经文的知识均告遗失的话,我们由这些引用的经句中仍可以重新编纂出一整部的新约全书。”33/86 盖司乐与尼克(Geisler and Nix)说: “引用之经文实在太多太广,即使没有新约抄本留存至今,单由早期教会早期领袖们的著作中,我们仍可以重新整理出一部新约圣经来。”14/357 盖司乐与尼克最后在其《圣经通介》(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中引用李齐(Charles Leach)所著的《我们的圣经是如何得来的》(Our Bible:How We Got it,pp.35-36)中戴平波爵士(Sir David Dabrymple)的一段话,当戴氏正在思量早期教会作品中超量的经文数量时,有人向他说:“如果新约圣经被人摧毁,至第三世纪结束前,每一部新约的手抄本亦均告遗失,我们单从第二及第三世纪教父们的作品中能否重新编出新约圣经来呢?” 经过长期的研究与考察,戴平波爵士(David Dabrymple)终于结论说: “现在请看这些书,你还记得所问有关新约圣经与早期教会领袖们作品的问题吗?那个问题引起我的好奇心,由于我个人拥有许多现存的第二、第三世纪教会初期领袖们的作品,我开始收集资料,至今为止,除了缺少十一节外,从他们作品中我几乎找到整本新约圣经的章节。”14/357 请留意:安格士(Joseph Angus)在《圣经手册》(The Bible Handbook)第56页中提及只使用教会初期的领袖们作品收集新约圣经所可能面临的一些困难。
教会初期领袖(犹太教法典)俄利根(Origen)在De Principus第二卷第三章中称罗马的克利门(Clement of Rome,公元95年),是使徒们的学生。4/28 另一教会初期领袖特土良(Tertullian)在《真道辩》(Against Heresies)第二十三章中,亦称克利门是使徒彼得所挑选的门徒。 爱任纽(Irenaeus)在《真道辩》(Against Heresies)第三卷第三章中说:“他仍有门徒的讲道回响在他耳中,他们的教训曾留在他眼前。” 他引用下列诸书卷: 马太福音 哥林多前书 马可福音 彼得前书 路加福音 希伯来书 使徒行传 提多书 伊格那丢(Ignatius),在公元70-110年间曾任安提阿教会总督,后为主殉道。他深识耶稣的门徒,也是坡旅甲(Polycarp)的学生,他的七篇书信中曾分别引用新约圣经中以下各书卷:
坡旅甲(Polycarp,公元70-156年)八十六岁时为主殉道,曾任士每拿(土耳其西方一海港)教会总督,是耶稣门徒约翰的学生。 巴拿马(Barnabas,公元70年) 何马斯(Hermas,公元95年) 塔弟安(Tatian,公元170年) 爱任纽(Irenaeus,公元170年)曾任里昂教会主教。 亚历山大城的克利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公元150-212年),他除有三本书未引用过之外,曾引用新约全书中经节达2400句之多。 特土良(Tertullian,公元160-220年)曾是非洲迦太基城教会的长老,其作品中引用新约圣经章句达七千余次,其中有3800句来自四福音书。 海波里多(Hippolytus,公元170-235年)引用1300多句新约经文。 犹斯丁(Justine Martyr,公元133年)曾极力与公元二、三世纪的马吉安异端Marcion相抗,马西翁异端不信旧约圣经与大部分的新约圣经。 俄利根(Origen,公元185-253或254年)这位善辩的作家曾写成六千多本作品,其中列举1万8千多句的新约经文。32/253 赛伯令(Cyprian,死于公元258年)曾任迦太基主教,引用740句旧约经文及1030句左右的新约经文。 盖司乐与尼克(Giesler and Nix)最后结论说:“只要我们略加统计就可以发现,在教会于公元325年举行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ea)之前,这些基督教教父们已经引用过3万2千多次的新约经文。这还不是全部的经文来源,因为第四世纪的其他作品尚未包括在内。如果我们将在尼西亚会议之前及会议同时的闻名作家优西比渥(Eusebius)的作品也加入计算的话,所被引用的新约经文数目则要超过3万6千的数字。”14/353-354 除上列所举的早期作家外,你尚可再加入奥古斯丁、安马比亚(Amabius)、赖汤帝纳(Laitantinus)、奎实顿(Chrysostom)、耶利米(Jerome)、罗曼拿(Gaius Romanus)、亚山那西(Athanasius)、米兰的安伯罗(Ambrose of Milan)、亚历山大城的西瑞(Cyril of Alexandria)、叙利亚的以法连(Ephraem of Syrian)、波易特的海拉瑞(Hilary of Poitiers)、乃沙的格里哥利(Gregory of Nyssa)等人。 我建议读者购买盖司乐与尼克(Giesler and Nix)所著的《圣经简介》(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Bible,Moody Press出版),他们在研究圣经抄本的权威性上下过极大的功夫,颇值得我们细读。 早期教会领袖作品中引用新约经文的次数
这是最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地区,却也是包含新约圣经抄本最多的一种文献。莫志杰(Bruce Metzger)对这些用来诵读的经文的背景这样解释说: “按照犹太会堂的惯例,每当在安息日聚会时,犹太人总要诵读一段律法及先知书。早期的基督教教会也沿习犹太人的惯例,在崇拜聚会中朗读一段新约圣经的章节,根据四福音书及新约中的书信篇,教会编出一个有系统的朗读课程。以后因循成习,在各主日及每年特殊的节日中,新约圣经被排成固定的次序,被人在教会中诵读。”33/30 莫志杰继续说,这些朗读资料中有2135种抄本已编入目录,但仍有不少有待仔细研讨与分析。 葛林理(H.Harold Greenlee)说: “最早朗诵抄本的片断来自第六世纪,成册的抄本则来自第八世纪之后。”19/45 一般的朗诵来源具有保守性,且采自较古的经文抄本,因此在经文批判学上颇有价值。33/31 旧约方面的参考文献,不似新约圣经那么丰富。直到死海经卷被发现之前,我们所拥有最早的希伯来文手抄本是来自公元900年左右。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是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时所写成,因此所留传下来的手抄本与原文相隔约有1300年的时间。乍看起来,似乎旧约圣经并不比其他古典文献来得可靠(比较世俗文典文献原著与手抄本相距之时间)。 然而当死海古卷被发现后,圣经学者才发现,许多旧约经卷都是在耶稣时代之前所写成的。 当这些事实被公诸于世,并经比较后,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印证旧约经文的可靠性。正如甘扬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所说的,“我们基督徒可以将圣经拿在手中,而毫不畏惧、也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手中握着的乃是上帝真实的话语,由历代相传下来的,虽经长久的年代,其中主要内容却从无损失。”25/23 首先,我们若要研究旧约的可靠性,我们就要仔细查考抄写经文的文士们,在抄写旧约圣经时所持的无微不至的态度。 1C.编纂犹太遗传经典的时代(The Talmudists,公元100至500年) 在这段期间,犹太人花费了极多的时间来编纂希伯来的民法和律法。编集犹太会堂中的经卷乃是一项极费力的繁琐工作。 戴维森(Samuel Davidson)在《旧约圣经的希伯来经文》(The Hedrew 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2 nd.ed.被录于詹姆郝斯丁[James Hastings]的《圣经字典》第四卷第949页中。)中描述一位犹太经典编纂家所必须遵守的严格纪律,我采用盖司乐和尼克合编的数码列举如下: 1.凡是犹太会堂中所用的经卷一律必须抄写在清洁的兽皮之上。 2.必须是由犹太人专为会堂聚会用而预备的。 3.这些经卷必须用清洁的兽皮所制成的皮带系在一起。 4.所有的经卷中,每一张兽皮中所包含的段数均需一致。 5.每一段落的宽度不得少过四十八行,也不得多过六十行,每一行长度不得超过三十字。 6.全本均需划行抄写,若头三字写成时未划行则必须作废。 7.抄写时所用的墨水必须是黑色的,且须照一定的配方制成,不得用红、绿或其他颜色的墨水书写。 8.抄写用的范本必须是真品,抄写时不得任意修改其中字句。 9.抄经之人必须看范本抄写,不可有一字,一字母,甚至一捺出自记忆……。 10.每个子音之间须留有细微的空间。 11.每段间应留有九个子音空隙。 12.每一卷书之间要留出三行的空隙。 13.摩西五经中的第五经末尾结束时必须划出一行,其他各书则不必如此。 14.抄写之人在抄写时必须穿戴犹太人的服装。 15.抄写前必须沐浴更衣。 16.新沾墨水的笔不可用来写上帝的名字。 17.当写及上帝的名字时,即使有王来对他说话,他亦可置之不理。 戴维森(Samuel Davidson)又说: “凡不依以上规定写成的经卷应放弃不用,将它埋于土中或予以焚毁,或被贬入学校当作教本使用,却不能用在会堂中。” 为什么我们没有更早的旧约手抄本呢?当我们注意到抄写古卷的人所必须遵守的规定或抄写时的准确性时,再注意早期旧约抄本的缺乏时,我们就可以明白现今所有旧约手抄本的可靠性了。 抄写犹太经卷的文士们对他们抄写的准确性颇有信心,他们相信这些副本完全如正本一样地具有权威性。 甘扬爵士(Frederic Kenyon)在《我们的圣经与古代手抄本》(Our Bible and The Ancient Manuscripts)也论及以上的记载及手抄本被毁的原因:“由于犹太人对抄写旧约经卷有极严格的要求,这也就是早期抄本消失的原因。当文士按照犹太法典的规定以极严谨的态度抄成旧约经卷,又经证实其中完全无误后,抄本就被当作正本一样看待,每一部抄本均一视同仁。这样一来,时间不但不能被用来考证抄本的真伪,反而变成一个弱点,因为抄本经长久使用后,必有所残缺,一有残缺的抄本便立刻被视为不合使用,必须予以废弃。 “在每个犹太会堂中均有一个木制的板柜,称之为Gheniza,其中专门用来存置残缺的旧约抄本,好些现存的最早旧约抄本都是在这种板柜中找到的。由此可见,犹太人习惯视新抄本较旧抄本更为可贵,因为它们是完整无缺的。而板柜中的残本则往往因忽略而腐坏,或因板柜中残本累积太多后被拿去埋了。 “我们不必为缺乏希伯来文最早的圣经抄本而感到惊讶,也不必为之不安。除了以上所述犹太人摧毁手抄本的方法外,我们还要记得,历世累代以来犹太人经常受到外族的迫害,他们的财物受摧毁,旧约手抄本的古卷当然也会随之丧失。而真正得以遗留下来的 ,就是犹太人视为所应当留下来的马所礼经卷(Massoretic text)。25/43 “犹太人对经卷的崇敬,对经卷纯正性的重视并不是在耶路撒冷城沦陷后才开始的。”18/173 我们从旧约的以斯拉记七章6节及10节就可以看出,其中称以斯拉说,“他是敏捷的文士。”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专才,一个对旧约有研究的人。 2C.马所礼的年代(Massorectic Peiod,公元500至900年) 马所礼人(The Massorectic,来自Massora一字,即“传统”的意思)专门从事编辑、校订旧约经文的辛劳工作,他们的总部在犹太地的提比哩亚海(即加利利海)附近,他们所编成的旧约经卷称之为马所礼经卷(Massoretic text)。 这些精心劳苦所编成的经卷,加上母音的拼音符号,以便帮助读者能正确发音之用。马所礼经卷乃是今日标准的希伯来文经卷。 马所礼人纪律十分严谨,一向存着极虔敬的心抄写经文。他们设计出一套十分复杂的系统,防范文士抄录时所可能产生的差误。比方说,他们计算每部书中每个字母出现过的数字,并计算出摩西五经与整本希伯来文圣经全文中间的那个字母是何字。除此之外,他们又设计了更多、更精细的计算方法,以防抄写时可能发生的任何错误。陆平费(Wheeler Robinson)在《古版与英文版圣经》(Ancient and English Version of the Bible,1940年出版,第29页)中说道:“任何可以数算的,他们都予以数算。他们还设计一种背诵法,将各处数目的总和很容易地全部记下来。”6/117 甘扬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说: “除了要记得手抄本的差异、传统与猜臆上的差异外,马所礼人还要着手于数字的计算,这些则是一般经文批判家们所不曾使用过的方法。他们记下每卷书中句数、字数及字母数目的总和各有多少,他们也计算出每卷书中间那个字和中间每个字母为何;他们知道那些经节包括有全部的希伯来字母,或只包括某些字母的经节等等。这些细节听来十分琐碎,但对抄写经文时,保持抄本的精确性却甚属必要。这些细节正表明人尊敬圣经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是理当受人颂赞的一本书。马所礼人唯一关心的乃是律法中的一点、一捺、一句、字母中的一小部分都不被抄漏。”25/38 魏洛狄(Robert Dick Wilson)在《科学化的旧约研究》(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Moody Press出版)论及圣经的可靠性与可信性应可以回溯至旧约时代:“由一四四件自埃及文、亚述文、巴比伦文及摩押文音译成希伯来文的名字中,或由四十个由希伯来文译成以上各文字的名字(总共一八八件证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有2300年至3900年的时间,圣经中的专有名词从没有被译错过。最初的文士在音译这些名字时,必须使用最正确的语言学原则,使原名与译名极其接近,这充分证明他们的仔细与学术精神。更有甚者,希伯来人的作品能数世纪以来一直被抄经家不断抄写,也是在其他历史文献中所未有过的现象。”48/71 魏洛狄(Robert Wilson)又说: “自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400年间共约有四十位君王存在,每位都按其朝代先后记载……‘其中不但记有同国的其他君王,又有其他国的君王史记可供核对……旧约圣经中有关各君王的记载,其正确性实超出人类的想像之外,’若这只是出于偶然,那它只有750,000,000,000,000,000,000,000分之一全对的机会。”48/70-71 根据这个证据,魏氏总结说: “这个证据说明旧约的原版经文经过二千年的抄写后,仍能十分正确地留存给我们,这件事实不容我们忽略。这不但证明二千年前的原版圣经与二千年后的抄本几乎完全吻合是可能的,我们由巴比伦原本与二千年后之抄本文献所存的类似之处,又由相隔二千年的纸草经卷与现今版本的古典文学相较,只见少数内容上的出入,再看过去希伯来原文经卷中的犹太君王名,及外国名词如今仍很正确地被留传下来,我们实不得不佩服这种近乎科学的精确性,这个精确性更是有目共睹的。”48/85 布如斯(F.F.Bruce)相信“马所礼人所编纂的希伯来文子音经卷(最早的希伯来文圣经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直到马所礼时代,因不方便朗读才加入母音。)流传有近一千年的时间,但与原本相较时,却仍能保持惊人的信实程度。”6/178 葛威亨(William Green)总结说: “世间没有任何其他的古典文献象旧约圣经这样正确、精细地被抄录流传下来的,这种说法真是一点不错。”18/181 论到希伯来文圣经能被如此正确地抄写、留传、英国剑桥大学图学馆副馆长艾肯孙(Atkinson)说:“这几乎就象是神迹一样。” 第二世纪的犹太教法师阿克巴(Rabbi Aquiba)一心视制造最正确的经书为己任,曾如此说:“马所礼人正确地抄写经卷,成为保存旧约圣经准确性的一道防护墙。”21/211 开罗版本(Cairo Codex)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约在公元前895年间问世,是由马所礼人阿学的儿子摩西一家人所抄成(Moses ben Asher),其中包括前后先知书在内。6/115-116 列宁格勒先知书版本(Codex of the Prophets of Leningrad)约在公元916年抄成,其中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及十二卷小先知书。 最早的整部旧约经卷应是巴比伦帕测巴力拿版本(Codex Babylonnicus Petropalitanus)约在公元1008年抄成,现存于列宁格勒。它是在公元1000年前左右由一位犹太教法师阿学的孙子摩西的儿子亚伦将古版修正抄写成的(Rabbi Aaron ben moses ben Asher)。14/250 阿里波版本(Aleppo Codex)乃是最有价值的一份旧约手抄本,约在公元900年左右完成的。有一度被人认为遗失了,后在1958年所复得,可惜已受损坏。 大英博物馆版本(British Museum Codex),包括部分的创世记直到申命记,约在公元950年完成。 乐奇灵的先知抄本(Reuchlin Codex of Prophets)是由拿弗他利之子一位马所礼人(Massorete ben Naphtali)所抄。 甘扬爵士是首先提出这个大问题的一位学者,他问道:“这些我们称之为马所礼经卷的希伯来文旧约经卷抄本,系抄自公元前1000年时的另一抄本,这个马所礼经卷与旧约各书的原版之间究竟有无出入?”25/47 后来所发现的死海经卷能对这个问题提供最有力的答案。 在发现死海古典前的问题是:“今日的旧约圣经与第一世纪的抄本间究竟有多少差别?”换句话说,这些旧约经卷被人腾抄过这么多次,我们是否还能相信它呢? 究竟甚么是死海经卷呢? 死海经卷乃由四万个经卷的碎片所集成,有五百份经卷是由这些碎片中所重新拼凑起来的。 考古学家们另外发现许多圣经教训之外的书卷及碎片,使我们对昆兰(Qumran,死海西北方,是发现死海古卷的地方)宗教社会的情形增加了不少了解。《朱达开文献》(Zodakite Documents),《社会法则》(Rule of the Community)及《纪律手册》(Manual of Discipline)各书的发现使我们了解昆兰人民的日常生活及意义。在其他很多洞穴中,我们则另外发现许多有用的解经的资料。 死海经卷是如何发现的? 我愿引用尔勒(Ralph Earle)所著之《圣经是如何来的》(How We Got Our Bible,Baker Book House出版)中的记载,因尔勒对死海经卷的发现有极生动的描述: “死海经卷发现的经过,可算是近代最精彩的一则故事。在1947年二、三月间,一个百岛因(Bedouin)的阿拉伯牧童,名叫莫罕默德,他出去寻找一只迷失的羊。为了试试羊是否藏在洞穴中,他用一块石子掷进死海西边的一个崖洞里,此洞穴距离耶利哥城之南约有八哩之遥。但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听见石子打破瓦罐的声音。走入洞穴细察之后,他却发一个令人惊讶的情景。在洞穴的地面上有好几个大瓦罐,内中藏着许多皮质经卷,均系用棉布包裹保存的。因为瓦罐妥善密封的缘故,这些经卷无损地保存在近1900年的时间(它们很显然是在公元68年左右存入此洞穴中的)。 “这些死海洞穴中所发现的经卷,其中五卷被耶路撒冷城叙利亚东正教修道院中的红衣主教所收购,另外三卷则由该地希伯来大学的萨肯尼教授(Sukenik)所收购。 “当这些死海古卷发现之初,新闻界对此毫无所知。1947年11月间,就在萨肯尼教授收购三卷经卷及两个大瓦罐的前两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如此写着:‘这很可能是巴勒斯坦一带最大的一项发现,是我们从未敢期待过的大发现。’然而这么重要的话却未在当时公开发表。 “直到1948年2月,幸好耶路撒冷城的红衣主教,因不识希伯来文的缘故,打电话给耶路撒冷城的美国东方学研究学会,询及有关这些经卷的事。当时东方学研究学会的代理会长是一位名叫查伟(John Trever)的年轻学者,他也是一位优秀的业余摄影家。他辛劳、谨慎的拍摄下以赛亚书皮质经卷的每一段,这些经卷每一卷均有十英寸高,二十四英寸长。在亲自冲洗出底片后,他以航空邮寄了一部分照片给美国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的亚布莱特教授(W.F.Albright),亚氏一向被认为美国圣经考古学的权威人士。在他的回信中,亚布莱特教授这样写道:‘我衷心恭贺本世纪最伟大的一项经卷发现!……多么令人难信的一项大发现!此乃最真实的一份旧约经卷,世人丝毫不必怀疑。’亚氏鉴定该书卷约是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所写成的。“11/48-49 查伟(John Trever)后又引用亚布莱特教授的话说:“我相信这些经卷要较纳西纸草古卷(Nash Papyrus)更为古老我估计它是在公元前100年左右……”24/260 死海经卷的价值 人类所拥有最早的旧约手抄本是出于公元900年左右,那么我们怎能确定自公元32年耶稣世代之后的抄本也是精确无误的呢?我们就该感谢考古学与现今发现的死海古卷了。在死海古卷中有一卷其中抄写的是全本希伯来文的以赛亚书,根据考古学家的鉴定,它是在公元前125年左右写成。这卷死海古卷,要较我们所知最早的旧约抄本尚早一千年以上。 其余的死海经卷则约写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68年各不等。 死海经卷发现所造成的最大影响,乃是印证以赛亚书经卷(写于公元前125年) 与一千年后马所礼人所抄写之以赛亚书(完成于公元916年)在比较之下,两者完全没有差别。这正证明了抄经家们精确的程度,历时千年却无疏漏。 “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中的166个字当中,只有十七个字是有疑问的。在这十七个字中有十个字是拼法有别,对书中意思并无影响。余下七字中,有四字是文体的改变,如连结词的增减等,其余的三字母可并成‘光’字,被加在11节中,但对全文意义亦无大影响。何况此字由希腊七十士译本(LXX)及一号昆兰山洞中所发现的以赛亚书样本中都可印证(IQIS)。这样看来,经过一千年后全章166字中,只有一字(包括三字母)是有疑问的,但此字对经文的意义却无甚影响。”14/263 布如斯(F.F.Bruce)说: “在昆兰的石穴中,我们又发现一卷不全的以赛亚书,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之为‘以赛亚书B’,但它与马所礼经卷的以赛亚书却是如此相似。“6/123 亚契(Glason Archer)认为“将昆兰洞穴中的以赛亚抄本拿来,与我们标准的希伯来文圣经中的以赛亚书对照,字字相比,其相同者约占95%以上,其余5%的不同乃是出于失笔与拼法上的错误。”57/19 盖司乐及尼克(Geisler and Nix)曾引用鲍罗斯(Millar Burrows)在《死海经卷》(The Dead Sea Scroll,P.304)一书中的话说:“历经一千年的抄写工作,经卷的内容却无甚变动,这成为一件奇事。正如我论及死海经卷的首篇论著时说的:‘死海经卷最重要的地方,乃在它能印证马所礼传统旧约圣经的可靠性。’”14/261 犹太人离乡流浪时,他们极需要有一部用他们通俗语言所译成的一部旧约圣经,这就是“七十士译本”的由来,约在埃及王托勒密二世(King Ptolemy Philadelphia,公元前285至246年)在位期间所译成。 布如斯(F.F.Bruce)曾生动地描写此译本之名的来源。约在公元前250年左右(较实际地说,应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在埃及王托勒密二世的朝延中一位名叫亚里斯提亚(Aristeas)的官员致信给他的兄弟费罗克拉次(Philocrates): “埃及王托勒密二世是位爱好文学的人,亚历山大城中最伟大的图书馆就是他在位时所兴建的,此图书馆傲立世间,成为世界文化奇迹之一达九百年之久。此信中并记载法拉兰城的底马特亚斯(Demetrius of Phalerum)曾任托勒密王的图书馆员,导致埃及王对犹太律法书的兴趣。王令他差派一位代表去见犹太大祭司以利沙(Eleazar)。大祭司以利沙从犹太十二支派的每支派中选出六位译经的长老,携带着特别正确、美丽的旧约经卷,送至亚历山大城。这些长老受到皇家的礼遇,藉辩论显示出自己乃是博学渊源之辈。后来被送至法老的小岛中住下(该岛以其灯塔闻名),在七十二天中他们将摩西五经全部译成希腊文。经过开会及校勘研考后,他们将修好的译本呈献埃及王。“6/146-147 由于希腊七十士译本与现今我们拥有的最早马所礼旧约手抄本(公元916年)十分相近,使我们确定在1300年后,旧约依然保守着它的精确性。 我们由《伪经传理书》(Ecclesiasticus)及《安息年书》(Book of Jubilee)中发现七十士译本及旧约经文的经节,由此可见今日的希伯来经书与公元300年前的原文经卷实无大差异。 盖司乐及尼克(Geisler and Nix)在他们对人极有帮助的著作《圣经通介》(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Bible)一书中提出希腊七十士译本的四大贡献: “1.此译本缩小了希伯来语与希腊语间人民的宗教鸿沟。 2.此译本缩短使用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犹太人与同时使用新、旧约圣经的希腊语基督徒间的距离。 3.它乃促使宣教士把圣经译成其他多种语言及方言的开路先锋。 4.藉希腊七十士译本与希伯来文圣经对旧约圣经内容相近的看法,得以缩小了经文批评的鸿沟。”14/308 布如斯(F.F.Bruce)提到后来犹太人对七十士译本丧失兴趣的原因: “1.……因为自第一世纪以后,基督徒将它视为旧约圣经的蓝本,经常引用它来传布福音及卫道用。6/150 2.……约在公元100年左右,犹太学者另外编纂成一本希伯来文的圣经修订本,这也是促使犹太人对希腊七十士译本失去兴趣的原因……”6/151 此版本包含摩西五经,对鉴定旧约经文内容甚有价值。布如斯(F.F.Bruce)说 “若将撒玛利亚版本中的摩西五经与马所礼旧约经卷版本(公元九一六年)相较,观察其间相同之处,其间相差之处则显得无足轻重了。”61/122 8C.泰根译本(The TargumsK,手抄本出现在公元500年左右) 泰根一字原为“传译”之意,相当于旧约的意译本。 自犹太人被迦勒底人(即巴比伦人)掳去后,巴比伦文字逐渐演变成犹太人通用的民间语言,犹太人需要有用他们通俗语言所译成的旧约圣经。 当时犹太人的主要泰根译本有两种:(1)翁凯拉斯的泰根译本(The Targum of Onkelas;有人说这是犹太名学者海洛[Hillel]的学生翁凯拉斯在公元前60年所译),其中包括摩西五经;(2)乌赛亚之子约拿单泰根译本(The Targum of Jonathon Ben Uzziel)可能是公元前30年左右译成,包括旧约所有史记及先知书。 布如斯(F.F.Bruce)曾解释泰根译本的由来:“……公元前一世纪将近尾声,犹太人在会堂中朗诵希伯来文圣经时,也开始同时以口传的方式,将旧约经文意译成一般犹太人能懂的亚兰语,朗诵给会众听。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当一般犹太人渐渐遗忘自己的希伯来文时,若还想明了旧约圣经,将它翻译成百姓能懂的文字就成了必要的事。会堂中意译经文的翻译员,犹太人称之为Methurgerman,他们所朗诵的亚兰语经文称之为泰根(Targum)。 “……意译翻译员……不可自经卷中朗读意译文句,恐怕会众误把他口译的经文视为出自圣经本文。为了能传译的准确,译者每次传译摩西五经时不可超过一节,传译先知书时,一次不可超过三节。 就在这种朗诵过程中,泰根译本遂得以一一完成。”6/133 泰根意译本的价值何在? 安德生(J.N.D.Anderson)在《圣经──神的话》(The bible,the Word of God)一书中论到它们的价值,说:“早期泰根译经的价值是因它能用来证明希伯来文圣经的真实性,证实无论是在泰根译经问世之时或是今天,希伯来文圣经都是一样的可信的。”4/17 9C.米示那口传经卷(The Mishnah,写于公元200年) 米示那一字即“解释、教导”之意。其中包括犹太人的传统习俗及对口授律法之注解。是以希伯来文写成,被称为摩西律法之下的第二律法。14/306 其中所引用之经节与马所礼经卷中的经文十分相近,可印证马所礼经卷的可靠性。 10C.吉马拉口传经卷(The Gemaras;巴勒斯坦版本写于公元200年;巴比伦版本写于公元500年) 这些用亚兰文写成的经卷注释,主要是用来注释米示那经卷的,也间接证实马所礼经卷的可靠性。 米示那口传经卷加上巴比伦版的吉马拉经卷,组合成巴比伦版的犹太遗传经。(Babylonian Talmud) 米示那口传经卷+巴比伦版的吉马拉口传经卷=巴比伦版的犹太遗传经(Mishna+Bab.Gemara=Babylonean Talmud)。 米示那口传经卷+巴勒斯坦版的吉马拉口传经卷=巴勒斯坦版的犹太遗传经(Mishna+Palest.Gemara=Palestinian Talmud)。 11C.米德拉西口传经卷(The Midrash,公元100至300年间写成) 这是收集希伯来文旧约经卷中的信条而写成,其中多处经文均引自马所礼旧约经卷。 教会初期领袖俄利根(Origen ,公元185-254年)曾著有《四福音合参》(Harmony of the Gospels),分别列出六种不同版本之经文:希腊七十士译本、亚奎那抄本(Aquila)、喜欧戴仙抄本(Theodation)、谢梅起抄本(Symmachus)、希伯来文抄本及希腊文字译成的希伯来文抄本。 六种经卷中同时又包括犹太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的作品,费罗及朱达开文献(Philo and Zadokite Documents,即死海昆兰社区的文献)。“它印证在公元40年至100年间,的确有与马所礼旧约古卷相似的经卷存在。”55/148 1C.允许怀疑精神的存在 孟沃华(John Warwick Montgomery)针对此项考验说,如今文学评论家们依然按照亚里斯多德的标准来评论文学作品:“怀疑之心应该用在考证之物本身,评论家们却不应该擅用它来阻挡真理。”34/29 “除非作者已知文字内容自相矛盾或与事实相违,吾人必须张耳静听被分析文件的自辩声,而不应存着偏见,事先假定文献的真伪对错。” 何恩(Robert M.Horn)针对此点强调说:“想将‘难题’转变为有力的证据,用以推翻教条实非易事,因为并非凡表面上看来是矛盾的道理都有是错的。第一,我们必须确定自己已经完全了解经文,其中的字句及数目的意义。第二,我们已拥有这一方面全部所需的知识。第三,更进一步的知识,经文的研究与考古学的新发现都有已不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判断经文的真伪。” 何恩又说:“……经文上的难题并不证明它们是不可信的;没有解决的问题也不一定必然就是错的。这不是要叫我们小视困难之处,而是希望我们能获得一种新眼光透视难题。难题能引起我们继续推敲的好奇心,面临问题容易使我们虚心追寻最清楚的亮光。但除非等到我们对经卷有了全盘的了解,我们实在不能迷信地说:‘这是个已经证实了的错误,证明圣经并非绝对无误。’人人都知道,自本世纪以来,过去的许多‘断案’如今都已一一被推翻了。”58/86-87 这些见证都是看见的人自己写的,或是由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者的口述而来。 “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路加福音一章1-3节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彼得后书一章16节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约翰一书一章3节 “以色列人哪!请听我的话。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使徒行传二章22节 “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 ──约翰福间十九章35节 “该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彼拉多作犹太巡抚,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腓力作以士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聂作亚比利尼分封的王……” ──路加福音三章1节 “保罗这样分诉,非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作的。”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24-26节 布如斯(F.F.Bruce)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赖兰教席(Ryland Professor)的圣经批判及翻译学教授,论到“新约圣经这些直接资料的价值”时,他这样说: “最早期的传道人,知道自己见证的价值……因此总是重复地说:‘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他们得有把握才这样说。当时耶稣的门徒极多,他们记得那些是发生过,那些没有发生过。因此不象现今一些作者认为捏造耶稣的言行是件容易事,因见证人太多,当时写新约的人不容易随便假造。 “很显然,早期的基督徒对什么是耶稣的话,什么是自己的见解与判断一直很小心地予以分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中论到结婚、离婚这个复杂的问题时,很仔细地分辩何为他自己的建议,何为主耶稣所定决定性的原则,在某些地方他用:‘我说,不是主说。’有些地方,他用:‘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 “最早期的传道人所面临的不单是一群友善的见证人,见证人在也有对基督徒甚不友善的,但这些人一样熟悉耶稣的生平事迹与他的死。因此使徒们不可能说假话(更别说去捏造事实),因为这些不友善的见证人惟恐没有机会去揭穿他们的谎言。在早期使者的传道信息中,最大的特色是他们对自己所传的知识深具信心,他们不单只说:‘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他们还说:‘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使徒行传二章22节)如果他们所说的与事实相违,听众中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不会出来指出他们的错误么?”7/33,44-46 新约圣经中的各书卷,被今日的圣经学者视为是第一世纪中最有力的直接资料来源。34/34-35 保罗书信 公元50至66年 马可福音 公元50至60年,58至65年 马太福音 公元80至85年 路加福音 60年早期 约翰福音 公元80至100年 甘扬爵士(Sir Fredric Kenyon)说: “我们找到可靠的证据证明约翰福音在第一世纪结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维廉弗克司亚布莱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曾是世间最出色的圣经考古学家,他说: “我们可以强调,目前尚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新约圣经中任何一部书是在公元80年后写成的,虽然现今的新约批评家认为新约多半在公元130至150年间写成,比实际年代远了约六十年的时间。”65/136 孟沃华(John Warwick Montgomery)引用甘扬爵士在1963年1月18日的《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周刊上记者访问中的谈话,说:“按我个人的看法,新约圣经的每卷书都是由一位受过洗礼的犹太人所写,大约是在第一世纪的40至80年间写成,更可能是在公元50至75年间写成的。”34/35 1C.其真实性能否被肯定? “是否有其他的历史材料能肯定或否定圣经文内的证据呢?”34/31 换言之,除了经文本身所提供的证据,有否其他圣经之外的资料能肯定圣经的真实性? 早期教会领袖优西比渥(Eusebius)在其所著之《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Ⅲ.39)中收有使徒约翰的学生帕皮亚──海拉波立教会的主教(公元130年),自约翰得来的资料:“长老(即使徒约翰)常如此说:‘马可是彼得的翻译员,曾精确地记下彼得所说一切有关耶稣的言行、事迹。因为马可既非亲耳听过,亦未亲自跟随过主耶稣,他乃是后起之秀,诚如我所说,是随伴彼得的。彼得见机运用主的话语,但非有心编纂主的话。所以马可并没有记错,只是将他(彼得)的口述一一记下而已。马可只留心一件事,就是绝不删除他所听见的,也不增添任何假话。’” 帕皮亚(Papias )也提到马太福音,他说:“马太福音是有希伯来文(亚兰语)所写成的。” 爱任纽(Irenaeus)曾任里昂主教(公元180年),他是士每拿主教坡旅甲(Polycarp)的学生。(坡旅甲在公元156年时为主殉道,身为基督徒86年,是使徒约翰的学生)爱任纽写道: “根据托尔斯地的葛理哥利(Gegory of Tours),他(爱任纽)曾将里昂的人全都带领归主,甚至还差遣宣道士到其他未信主的欧洲地区去。” 在“真道辩第三卷”(Against HeresiesⅢ)中,爱任纽写道:“四福音书的根基十分稳固,甚至连异端邪说也见证这福音的根基,因为每一种异端,都是从福音书中收集资料来另创新说的。” 四福音书在当日基督教所传到的地区中,早已为众人所接受,因此爱任纽的著作中经常提到这些被人公认的道理,正如罗盘针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一样无法为人所否定,他说: “地球有四界,风有四向,当教会向全世界扩展时,福音就成了教会的栋梁与根基,也是人类生命气息之所系。它自然有四个栋梁,好像不朽的气息从每个角落点燃人的新生命,为向世人‘彰显’此道乃万物之建造者,坐在宝座之上,联系万物,并赐四福音将自己彰显给世人看。此四福音书虽分为四部,却同为一灵所联合。” 教会先父爱任纽(Irenaeus)继续说: “马太在犹太人当中写成马太福音,而彼得与保罗则在罗马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根据传说,当彼得保罗于公元64年左右,死于尼罗王手下之后,彼得的学生马可,兼翻译,将彼得讲章的文稿留下给我们。保罗的学生路加,则在所写的福音书中加入他老师的讲章。约翰是耶稣的门徒,是曾靠在耶稣胸膛上的那一位(参阅约翰福音十三章25节及二十一章20节),则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现今土耳其境内)写成约翰福音。” 蓝赛爵士(Sir William M.Ramsay)说:“路加写成的历史,其可靠性是无人可比拟的。”95/81 罗马的克利门(Clement of Roman,公元95年)视圣经为可靠、真实的,经常应用。 伊格那丢(Ignatius),在公元70至110年间,曾任安提阿(今叙利亚境内)教会主教,后因其信仰殉道。他认识耶稣所有的门徒,也是坡旅甲(Polycarp)的门徒之一,坡旅甲则为使徒约翰的门生。59/209 毛耶(Elgin Moyer)在《教会历史名人录》(Who Was Who in Church History,Moody Press,1968年出版)中写道:“伊格那丢自己说‘我宁可为耶稣殉道,也不愿意统治世界,抛我入野兽群中,我好藉它们在神的事上有份’。据说他果真在罗马被掷入斗兽场的猛兽群中,他所遗留下来的书信,则是他从安提亚出发往罗马殉道途中写成的。”59/209 伊格那丢(Ignatius)相信圣经,以圣经之正确性为其信仰的根基,他拥有大量的资料与见证能证明圣经之可靠性。 坡旅甲(polycarp,公元70至156年)曾是使徒约翰的门徒,由于他对耶稣与圣经至死忠心,终于在八十六岁时为主殉道。坡旅甲的死证明他相信圣经是精确无误的一本书。“公元155年当罗马大帝庇亚斯Antoninus Pius(138至161年)在位时,在士每拿一带有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他所在的教会中许多教友因此殉道。他被检举为教会的领导人物,被提出处死。迫害他的人劝他放弃自己的信仰,即可保全性命,他一口拒绝说:‘我事奉他86年,他没有亏待过我,我怎能毁谤这位拯救我的君王呢?’最后他被捆在木柱上,活活被烧死了。他因自己的信仰成为英勇的殉道士。”59/337 坡旅甲认识许多信徒,他显然是一位明白真理的人。 约瑟夫(Flavius Josephus)是犹太的史学家。 约瑟夫所描写施洗约翰所施的洗礼与福音书中所记载的略有不同,约瑟夫说施洗约翰所行的洗礼不是悔改的洗,但马可福音一章4节中却说是如此;约瑟夫又说施洗约翰之所以被处死是因政治上的原因,并非他批评希律王娶自己兄弟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布如斯(F.F.Bruce)指出,很可能希律期望一箭双雕,才把约翰下在狱中。至于对施洗的解释有出入,布如斯说:福音书乃是根据“宗教──历史”这两个观点所写成,要比约瑟夫写成的史书时间为早,因此较为确实。除了这些细节外,一般来说,约瑟夫的记载与福音书的记载都颇能相合。7/107 约瑟夫在其《考古文献》十八卷5章2节(Antiquity Xv Ⅲ.5.2)提到施洗约翰,由于这段文字写成的方式,其中实在很难有基督徒在其中增添字句的余地,这段文字如此记道: “现在有些犹太人以为希律的军队已被上帝摧毁了,这正是处死施洗约翰所应得的报应。他实在是个好人,但希律把他杀了。他曾吩咐犹太人行正当的事,彼此公平相待,虔诚敬拜上帝,并呼召犹太人前来受洗。他认为受洗是为上帝所接受的,这个仪式虽然不能洗去若干罪,但如果一个人的灵魂已经因自己公义的行为得以洁净,洗礼则有净化其身体的功能。当犹太人因听他的话受感动,开始拥护他时,希律王怕他的说服力,足以号召百姓起义叛变,因这时百姓似乎完全听他的指挥。于是希律王想最好是立刻捉拿他,乘他在造反之前将他处死,以免事情真发生后后悔不及。由于希律王的多疑,施洗约翰被下在前文所提及的马丘路(Machaerus)碉堡中,最后在那儿被处死。犹太人相信希律军队遇难,乃是上帝为施洗约翰报仇之故。”7/106 塔弟安(Tatian,公元170年)是亚述的基督徒,他曾将圣经编纂起来,写成第一部“四福音合参”,希腊文为Diatessaron. 第二部分 考古文献印证圣经的可靠性 犹太名考古家学葛鲁克(Nelson Glueck)写道:“我可以很肯定的说,至今所有考古学上的发现,都没有一项是与圣经文献相抵触的。”葛鲁克又说:“圣经中有关历史记载的正确性是无可比拟的,尤其当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15/31 亚布莱特教授(Wiliam F.Albright)是世间闻名的考古学权威,他说:“无疑的,考古学已经证实旧约圣经传统具有绝对的历史性。”64/176 亚教授又说:“当十八、十九世纪期间,许多重要的历史学派都怀疑圣经的可靠性,虽然今天仍有一部分当时的学派偶然又重复地出现于学术界,但早期怀疑学派之说均已逐渐被否定了。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一再印证圣经中许许多多细枝末节的部分,使人们重新认识圣经乃是查考人类历史的一部最好资料。”2/127-128 孟沃华(John Warwick Montgomery)在“福音派人士与考古学”一文中(Evangelicals And Archaeology)讨论到今日学者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时,说:“美国圣地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Holy Land Studies)的研究员曹北拿(Thomas Drobena)提醒我们说,考古学家与圣经之间所起的最大争执,就是关于年代的鉴定问题,这也是今日考古学家们觉得最无把握的领域,这里科学的演绎说与自己的自圆其说往往取代实际实验上的分析。”64/4-48(上文摘自“今日基督教”杂志) 魏思曼(Donald F.Wiseman)在卡亨利(Carl Henry)所编的《启示录与圣经》(The Revelation and the Bible,Baker Book House,1969年出版)一书中引用罗列教授(H.H.Rowley)的话说:“今天的学者并不比前一代的学者持较保守的假定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他们也不见得比过去的学者对圣经中的故事持较尊敬的态度,只是因考古学证据俱在,使他们责无旁贷。”62/305 翁格(Merrill Unger)在《考古学与新约圣经》(Archaeosogy and the New Testament,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1962年出版)中说道:“新旧约圣经考古学的研究,其目的在加速科学上的新知识,平衡批判圣经的理论,说明、阐述、加强并鉴定圣经与世界历史及文化背景间的关连性,希望为未来圣经内容的批判上带来光明的一环。”88/25-26 耶鲁大学的鲍罗斯(Mollar Burrows)注意到:“考古学好些时候驳倒新派的圣经批判学说,证明他们的学说多是建立在不正确的假设之上,及一些不真实与人为的历史发展程序中,这些考古学上具体的贡献实不容我们忽视。”68/291 布如斯(F.F.Bruce)说: “凡是别人猜疑路加所记为不属实的地方,考古学所掘出的碑文都证实它们是可靠的,由此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考古学可以证实新约的记载。”86/331 翁格(Merrill Unger)曾如此结论说: “根据新约圣经的资料,考古学家们曾掘出好几座古代的城市,发现过去被人视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考古学以惊人的手法增添我们圣经知识的背景,也填补了历史上的空白部分。”88/15 亚布莱特教授(William F.Albright)继续说: “圣经的批判研究深受近来大量自近东发掘的资料所影响,我们慢慢可以看见,今日仍为人忽视或渺视的新旧约经文,终有一天要被人视为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了。”2/81 鲍罗斯(Millar Brrows)论及不信者所以怀疑的原因:“许多自由派学者之所以怀疑圣经,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现存的考古资料作过任何仔细鉴定的工作,而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根本就反对任何超自然的事迹。”79/176 这位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继续补充说:“然而全面来说,考古学上的发现无疑地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许多考古学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而使自己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68/1 “一般来说,这些考古学上的证据,尤其是新近发现较古的圣经古卷,实在增强我们对圣经能历经辗转腾抄欲不失其真的信心。”68/42 甘扬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说: “因此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说,十九世纪末叶那些企图破除旧约中某一部分经文的学说,如今已不能存在,考古学的证据重新肯定圣经的权威性。同时,由于考古学的证据能提供我们对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情况的完整知识,我们因此看出圣经的价值。考古学的工作至今尚未全部完成,但藉现在已挖掘出来的证据,我们看见它已经印证我们信心的确据──圣经的真实性能随着人类知识日增而更为彰显。”56/279 考古学也发掘出大量的证据,证实犹太人马所礼经卷的准确性。 兰姆(Bernard Ramm)在“耶利米的封印”(Jeremiah Seal)中写道:“考古学一直提供证据,证实我们的马所礼经卷的准确性。耶利米封印乃是印在一个酒罐的沥青封条上,估计是在公元第一或第二世纪时印上的,封条上印有旧约耶利米书四十八章十一节的经文,内容与马所礼经卷的经文完全相符。此‘封印证明抄写准确的程度,且没有因时间上的差距使内容有所改变。’除此之外,公元前第二世纪罗拔士纸草经卷(Rorerts Papyrus)与亚布莱特教授鉴定是出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纳西纸草经卷(Nash Papyrus)也都能与马所礼经卷相符合。”37/8-10 亚布莱特教授(William Albright)也肯定兰姆的发现说: “我们可以很肯定地相信,希伯来文的子音经卷,虽然不能说是绝对无误的,但其所保存的精确性仍是任何其他远东古典文献所望尘莫及的……最近由叙利亚西方所挖掘出来的乌格里文献(Ugariticliterature)已经印证各时代的希伯来文圣经,其中的诗词不但能一直保存着原有的古色,抄写者的准确性也实在令人敬佩。“63/25 考古学家亚布莱特(William Albright)在《巴勒斯坦的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Pelican Books,1960年出版)一书中论及考古证据印证圣经之可靠性时,他说: “摩西五经所叙述的内容远比摩西写完全经的日期早许多,考古学家所挖掘的证据一再印证其中内容及文体的真实性……只有假说能否定摩西时代的人物并不存在。”61/224 亚布莱特在《亚伯拉罕至以斯拉的圣经时代》(The Biblical Period form Abraham to Ezra,Harper,1960年出版)一书中继续说,圣经批判家常这样说:“直到不久以前,圣经历史家们常习惯视创世记的人物为这个分裂的以色列王国中文士们手创的故事,或是想象力丰富的狂士们,在侵占这个国家数百年后围着以色列人的营火所说的故事。许多鼎鼎大名的学者们都视创世记十一章至五十章为后为之产品,或是对早已消逝的王朝所编造出来的故事或情节。”67/1-2 亚布莱特教授说:“但如今一切都改变了,1925年以来,在考古学上的新发现推翻这一切的假设。除了少数较顽固的一些老学者外,几乎没有一位圣经历史学家不为与日俱增能用来支持以色列支派传统历史的证据所感动,根据创世记的记载,以色列民族的祖先,早在公元前二千年的末期及公元一千年前的头一世纪时代,已是外约旦──也就是叙利亚、幼发拉底河盆地及阿拉伯北方民族的近亲。”67/1-2 鲍罗斯(Millar Burrows)继续说: “要想看清这件事实,我们应该明白这些考古资料可以肯定两种不同范围的事实:一般性的与特殊性的。所谓一般性的肯定是指事物大体能相合,而不求细节上的相应。以上我们所讨论的可以用在一般性的肯定上,等于图有了,框子也能配得上,音乐的旋律与伴奏均能和谐。这类的证据层出不穷,我们从圣经中找到的物件愈多,考古学上所能印证的也愈多,我们对圣经的真确性也能愈俱信心。若圣经仅来自传说或小说式的构想,无疑地,终久必要露出马脚来。”68/278 1E.创世记中记载以色列人的祖先是来自米索不达亚一带,这点与考古学上的发现完全吻合。亚布莱特(W.F.Albright)说:“希伯来人原来是来自米索不达米亚西北方的白立克山谷(Balikh Vslley),这点是无法否认的。”考古学家曾返溯希伯来人的历史,发现他们果真是自米索不达米亚一带迁移出来的。67/2 2E.按照旧约圣经的说法,“在建造巴塔之前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创世记十一章1节),后来上帝毁坏该塔、变乱天下人的言语(创世记十一章9节)。而今天许多语言学家也同意,世界的语言很可能是同出于一源。龚百地(Alfredo Trombeti)说,他已经追溯出世间所有语言均出于一源。莫勒(Max Mueller)也证明语言之同源说。杰斯波生(Otta Jesperson)更进一步地说,是上帝把语言赐给第一代的人。72/47 3E.在以扫的家谱中,提到何利人(创世记三十六章20节)。曾有一段时期,何利人被视为“居住在洞穴中的人”,因为希伯来文中何利与洞穴二字十分相近。但如今考古学家证实在早期以色列历史时代,确有何利人居住在近东一带,他们都是能战的武士。72/72 4E.考古学家贾时谭(John Garstang)在1930年至1936年挖掘耶利哥城的时候,发现一件惊人的证据,他甚至与其他两位考古学家联合签字,记下他们的新发现。贾时谭这样写道:“我们对主要的一件事现已毫无异议:耶利哥城的城墙确实是向外倒的,因此城外的兵士可以爬过倒墙,进攻城内。”这点又有何特别呢?特别的地方是,一般的城墙多不向外倒,却是向里倒的。但约书亚记六章20节中却说“……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耶利哥的城墙是上帝使它向外倒的。90/146 5E.我们又发现亚伯拉罕的家谱具有绝对的历史性。我们不明白的是,这些名字究竟是代表人呢?还是代表不同的城市?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亚伯拉罕是个人,他确实存在过。鲍罗斯(Millar Burrows)说:“考古学的证据处处指出亚伯拉罕是位历史人物,在已知的考古文件中没有提及此人,但是与他同时的巴比伦文献中有他的名字出现过。”68/258-259 早先有人想把亚伯拉罕的时代挪至公元前十四或十五世纪,这与他存在的时期相比要远得太多。但是亚布莱特(W.F.Albright)指出,“以上巴比伦的资料以及一些其他的资料,使我们拥有大量的人名与地名的证据,印证更改亚伯拉罕存在的时期实无必要。”67/9 6E.虽然至今考古学家们尚找不出早期以色列族系统治国的证据,但我们所找到的社会、风俗文献与当初以色列国的故事颇能吻合。68/278-279 一些有关民情风俗的资料来自挖掘拿佐(Nuzu)与马利(Mary)两城。乌格里(Ugarit)的挖掘工作使我们对希伯来人的诗歌与文字有进一步的了解。摩西的律法我们可以自古叙利亚带的赫提特(Hittite)、亚述,幼发拉底河下游的萨姆里及以修纳(Eshunna)法典中看出来。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见希伯来人与其周围的民族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诚如亚布莱特教授所说的:“这个发现实为考古学上的一大贡献,使其余的都显得微不足道了。”63/28 无论这些考古学家们宗教信仰如何,他们均一致承认这些早期的希伯来人祖先都是可以证实的一些历史人物。 7E.魏豪生(Julius Wellhaussen)是十九世纪一位有名的圣经批判家,他觉得摩西颁布的大祭司条例中,论到用圆铜镜制洗濯盆很可能是后人加入的资料,为配合他的这种看法,他不得不把记载帐幕的时间挪得再后些。只是当时我们没有肯定的资料,证明魏豪生所定的时期(公元前500年)不对。但后来我们发现从埃及历史的帝国时代中确实找到有关铜镜的记载(时间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1200年间),由此我们推出摩西与出埃及记亦属此时代的事迹,即公元前1500年至1400年间的事。72/108 8E.亨利莫理斯(Henry Morris)在《圣经与现代科学》(The Bible and Moden Science,Moody Press,1956年出版)一书中如此注意到:“我们不能否认,考古学所发觉的资料与圣经上的记载仍有不能完全吻合的地方,但其中的差异并不严重,只要我们肯继续下功夫,问题总有解决的一日。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考古学家挖掘出许多与圣经背景有关的证据,然而直到今天,其中尚没有一件能证明圣经是错的。” 1E.路加所记载的历史,其可靠性已不足怀疑。翁格(Merrill Unger)告诉我们考古学家已充分证实福音书的记载,尤其是路加作品的真实性。翁格这样说“现在学术界均一致同意,使徒行传为路加所著,大约是在第一世纪前写成,路加以一个史学家的工作态度从事写作,且曾正确地使用各式可靠的参考资料。”88/24 蓝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被人视为世间最伟大的一位考古学家。他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校中受教,在校期间他从学习中知道使徒行传乃属公元第二世纪中叶的作品,他不仅深信此说,并且决心要证明此说。然而经过他的努力,收集来无数的证据之后,他反而推翻了自己以往的信念,他这样解释:“当我最初开始从事此项研究工作时,丝毫没有想到路加的作品应属第一世纪。相反的我反对这种说法,别出心裁与听起来完善的托宾根(Tubingen)理论完全把我说服,我已没有兴趣对使徒行传写成的时间再去仔细研究。直到近来因研究小亚细亚一带的地势、古迹及社区情况,我才再度有机会详读使徒行传,无意中却发现其中的记载竟是出人意料的真实。事实上,我一直视此书为公元第二世纪的作品,根本不信其中所包含的证据能印证第一世纪时的实况,但我却慢慢发现这本书实在是研究费解难题的良友。”(上文引自蓝赛爵士所著之《罗马公民与旅行家──保罗》(St.Paul the Traveler and Roman Citizen,Baker Book House,1962年出版。)94/7-8 蓝赛也对路加写作历史的能力甚为佩服: “路加是一位第一流的史学家,他所写的资料不但真实可考,他也拥有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控制历史演进的一些理想和计划上,又能适当的处理每一件重要的历史事迹。他能掌握住重要的事件,据实长谈,对不足轻重的史迹,他则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有些则完全删除不记。总之,路加的名字应与世间伟大的史学家同列。”91/222 有一度史学家们认为路加在描绘耶稣诞生前的情形时(路加福音二章1至3节)离谱太远。他们找不出历史上有申报户口的事,居里扭未曾作过叙利亚的巡抚,当时百姓也没有要各归各乡的事。70/159,160;29/185 但是考古学家们以后发现,在罗马帝国中每隔离十四年,均有一次人口调查,确实有要求付税人报名上册的事。这条法令是在罗马大帝亚古士督在任时开始的,首次或在公元前23至22年,或在公元前9至8年时举行的。路加所指的可能即后者。 其次,我们找到居里扭在公元前7年左右,任叙利亚巡抚的证据。考古学家们根据在安提阿找到的一块碑文,其中刻有差派居里扭任巡抚职位的记载。我们依此证据相信居里扭曾俩度任叙利亚巡抚,一次是在公元前7年,一次是在公元后6年(约瑟夫的估计)。70/160 最后,有关报名上册一事,我们在埃及的纸草卷上发现载有户口登记的规条。 其上写道:“由于报名上册之时已近,凡因故远离家乡,远居各地之人都应准备回乡,以便完成全家户口登记的手续,才可保留属他们的耕地。”70/159-160;72/185 考古学一度认为路加在使徒行传十四章6节中的记载有误。因为路加说路司得和特庇二城属吕高尼,但以哥念不在吕高尼地。而罗马其他作家如西赛禄等的作品中则提到以哥念城确实在吕高尼,因此考古学断定路加的记载不实。在1910年时,蓝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却找到一个纪念碑,其中说到以哥念乃是小亚细亚的一座古城,以后考古学上的发现也印证路加的记载原是正确的。72/317 另在路加福音三章1节中,路加提到当施洗约翰开始传道之时,时间大约是公元27年,是“吕撒聂作亚比利尼分封的王”的时候。但史学家唯一能找到的吕撒聂王却在公元前36年时已被人暗杀而死。以后考古学家在大马色城附近发现一块碑铭,其上列有“吕撒聂分封之王所释放的奴隶”等字样,根据考证,此碑文是刻于公元14至29年间。89/321 当保罗在哥林多城写罗马书时,他提到哥林多城的司库以拉都。1929年当哥林多古城被发现时,考古学家们掘出一条马路,其上刻有“ERASTVS PRO:AED:S:P:STRAVIT”的字样,译出来即是(“以拉都,公共建筑物的监护人,出私款铺成此路”)根据鲍罗斯(Millar Burrows)的考察,此路可能是在公元第一世纪时所筑成,出资筑路之人与保罗所提及的司库,很可能同属一人。7/95;79/185 另外在哥林多古城中,考古学家们掘出一块碑铭的残片,经拼凑后,很可能是“希伯来人的会堂”几个字,也许是来自食堂大门上的匾额,保罗曾在其中辩论劝人信仰真道(使徒行传十八章4-7节)。此外他们还发现另一碑文残片,其上列有“肉市场”字样,很可能即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25节中所提及的地方。 感谢考古学家的辛劳,新约圣经中提及许多城市得以一一被证实。保罗三次的传道旅程,如今也可由考古学资料中很正确地追溯出来。7/95;65/118 路加曾提及以弗所城的暴动,及人们在一家戏院聚集的情形(参阅使徒行传十九章29节),由所发现的铭刻文字上,考古学家们发现,确实在一次大聚集时有人将银刻亚底米雕像(即希腊的戴安娜月神)“抬入戏院中”,证明保罗之话非假。随后所掘出的戏院,证实可容纳二万五千人。89/326 路加又记载耶路撒冷城中暴动的情形,因为以色列误以为保罗将一个外邦人带进圣殿当中(使徒行传二十一章28节)。同样考古学家发现有一片碑铭其上同时用希腊及拉丁文写道:“外邦人不可进入神殿外的栏栅,违者一律处死。”这又证明路加是对的!89/326 过去有些人怀疑路加的用字是否正确,因为他称腓立比是马其顿“这一方”或作“这一区”中的一座城(使徒行传十六章11节),路加选用希腊字meris,可译作“区”也可译作“一带”。何德(F.J.A.Hort)认为路加的用法欠妥,因为meris在希腊文中是“部分”的意思,而非“区”的意思,然而考古学上却发现meris一字确实是指按区划分的地界。可见考古学再度证明路加记载的正确性。72/320 又有人批评路加称腓立比的统治阶级为“民政官”(Praetors),“圣经学者”则认为当时的腓立比采用二头共治的政体。然而路加还是对的,从考古学的发现中,我们得知罗马属地的长官均称民政官。72/321 至于他称迦流为“亚该亚的方伯(地方长官)”(使徒行传十八章12节)也是对的,因后来掘得的戴费碑铭(Delphi Inscription),其上有记:“至于我们朋友迦流,则是亚该地方方伯……”79/180 公元52年刻成的戴碑铭(Delphi Inscription)又帮助我们肯定,保罗在哥林多布道一年半确为属实,其他资料中也印证这是事实。因为迦流是在7月1日上任的,他的官期仅一年,正与保罗在哥林多工作的一部分时间相合。89/324 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七节中,保罗称米利大岛(即今日地中海西西里岛南方的马耳他岛)的统治者部百流为“岛长”。考古学家所发掘的碑文亦称他为“岛长”。89/325 另外路加在使徒行传十七章6节中称帖撒罗尼迦的官员为“地方官”(Politarch),因古典文献中从未有这字出现,学者们就结论路加是错的,但以后有十九块碑文上列有“地方官”Politarch这个官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五个特别是指帖撒罗尼迦城而言。89/325 1945年在耶路撒冷城郊外,考古学家萨肯尼教授(Eleazer L.Sukenik)发现两个“骨瓮”(盛放遗骨之器),其上刻有字画,萨氏认为这可能是有关“基督教的最早记录”。这两个骨瓮是在公元50年的一座坟墓中找到的,其上写着lesous iou 及lesous aloth几个字并刻着四个十字架。头一句看来是向耶稣求助的祷词,第二句则是为骨瓮中此人之复活所献的祷告。89/327-328 无怪乎奥克兰大学(Auckland University)的古典文学教授柏莱洛克(E.M.Blaidklock)这样总结说:“路加是位彻底的史学家,他的独特之处使他可与世间其他希腊作家齐名。”12/89 2E.碎纹石小道(The Pavement),希伯来语叫厄巴大(Gabbatha,约翰十九章13节)。许久以来,人们一直找不出这个耶稣受披拉多审判的地方究竟何在,因此有人说:“看吧!圣经不过是神话,并没有任何历史根据。” 亚布莱特教授(William F.Albright)在“巴勒斯坦的考古学”(The Archaelogy of Palestine)一书中却指出此处就是耶路撒冷的罗马军事总部所在地,乃是一座称为安东尼之塔的公堂。该地在公元66至70年间当耶路撒冷城被毁时同时遭毁。以后罗国大帝哈德里安(Hadrian)(137至138年)在位时曾重建耶路撒冷城,却将该公堂埋在地下,直到近来始为人所发现。2/41 3E.毕士大池,这是新约圣经上另一处史无稽考的地名(约翰福音五章2节),现在考古学家们已颇有把握地相信,“此池大约座落在第一世纪时耶路撒冷古城的东北部(此区称为毕士沙,乃‘新草地’的意思。1888年左右考古学家们在圣安娜教会附近,挖掘时找到它的遗迹。”89/329 结 论 我个人原企图粉碎圣经的历史性及可靠性,结果却因此认识圣经在历史性上是绝对正确可靠的。如果一个人认为圣经是不可信的一本书,必须将之抛弃的话,那么除了圣经外,他恐怕要连所有的古典文学作品都要掷弃不用了。 我个人所面临最大的试探,我相信也是大多数人最易犯的一项错误,就是用一种标准来衡量通俗文学,却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圣经。其实我们该用同一尺度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不论它们是通俗性的,还是宗教性的。 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才有资格把圣经拿在手中,说:“圣经是可信的,是具有历史性的。” 瓦尔特司考特爵士的诗句可以说是恰当的概括了对圣经的评价: “那威严的书卷里展现着 一切奥妙的奥妙 人类历程中最福气的珍宝 上帝赐予的恩惠和教导 学习,敬畏,盼望和祈祷 卸掉门闩,向上帝的道路奋力奔跑; 最好是对那奥妙从来不怀疑或者轻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