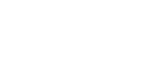肆 哲人的悔悟
柏拉图曾设一个比喻,说:「有一群困在暗无天日的山洞里的囚犯,手足都被捆锁,颈上戴了桎梏,行动既无自由,所见亦殊模糊,只能凭其猜测,妄加指称。后来有一个囚犯,得蒙开释,重见天日,确实看到各种实物本体之真像,始知以往的猜测,都属错误,便去告诉那些在黑暗中的囚犯。但那些囚犯,非但不信,还和他争辩。」柏拉图这个比喻,正足说明那些不信基督,不见真光,没有重生得救的世人之景况。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既对真理模糊不清,且复执持偏见,以伪乱真,这正同那些在暗无天日中的囚犯,同样可悲。
哲学并不是真理,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580-500 B.C.),虽被其门徒奉若神明,但毕氏仅自称为「爱智者」,并谓「智慧乃属上帝,并非属人」。奥古斯丁复认为柏拉图和新柏拉图派之创始者柏落第(Plotinus),都想用自我神化的方法,寻求上帝,乃为绝不可能之事。「因为人乃被造之物,只能靠着神的恩典,始能和神性有份。人既非神,真理亦既属神,自不能从人求得真理。」人既非自有永有,一个本来「没有」、「终必归于无有」的人,想单靠人的理性去了解超越的「自有永有」的上帝,这乃是一种绝不可能的妄想,亦为「内在哲学家」所以心劳日拙、终归虚空的悲哀。有人以哲学家比诸一位想在一间根本没有猫在里面的暗室中捉猫的人,实属简明确当。又据卡夫卡(Kafka)寓言,谓有一人,独行旷野,偶见大厦,入内参观,发现一人在澡盆钓鱼。审视久之,因向进言:「盆既无鱼,终日垂钓,岂非徒劳!」其人慢声应曰:「余亦知之。」此人明知无鱼,但仍垂钓自若。此亦正足表明世俗学者,执迷不悟,自我陶醉之情态!法国天才科学家巴斯格氏(Pascal)初亦想从科学哲学探求人生奥秘,卒陷非常烦闷痛苦的境界,乃废然而返,研读圣经;果于某夕看到神的荣光,像摩西所见之火焰,充满其室,并得神启示,上闻主声,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
诚以宇宙本身,已是伟大奇妙,非人智所能窥测,则我们对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自更无法了悟。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约三12)「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罗一一33;并参阅伯一一7)「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了面对面看到「那完全的来到」的时候,「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林前一三8-12)。史宾塞(H. Spencer)亦尝说:「我们的心智和思想都是有限的,绝对不能对那位超乎一切限制者,来加以概念的说明。」可见科学哲学实不能解答宇宙人生的问题。所以基督教非科学非哲学,而乃为神的启示,而有其独特的宇宙观。主耶稣所讲关于上帝的道理,绝非文学的空谈,所以不用「无限者」(Infinite),「绝对者」(Absolute),「第一因」(First Cause),「超绝者」(Unconditioned)那些陈腐的玄学名词。这些玄学名词,乃是本节上文柏拉图比喻中那些在岩洞里的囚犯,在暗无天日中所揣摩的暗影,而非其所指的本体的真像。甚至谢林(Friedrich W. J. Schelling)也说,基督教并非空洞的学说,乃为客观的事实。基督教最主要的内容与实质,乃为基督,非在空洞的理论,乃在基督所完成的救恩。这乃是基督教所以异乎一般宗教和哲学的特点。基督教的宇宙观,其中心乃在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这一个观念非常重要,因为他乃是「上帝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来一3)他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一15-17)所以渥尔博士(James Orr)说,主耶稣基督乃是宇宙的中心,而且也是哲学的中心。又谓:如果承认他是宇宙的中心,便能引导人类向上(Upward Movement),有正确的上帝观,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和上帝(约二○28),从而真正明白上帝的启示。因为主耶稣也曾明言:「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约一四1)但是,如果不信主耶稣,或虽信却又不信他完全的神性,则其境界,必每况愈下,日趋沉沦(Downward Movement)。从一种「凡人论」(Humanitarianism),或「不可知论」流为「怀疑主义」,甚至「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例如伏尔泰(Voltaire),他不信耶稣,所以他晚年非常悲观,对人生亦无兴趣,认为这个世界只是充满了尸体,并怨叹他生在世上。而当他临死之时,看到黑暗迎面压身,便战栗惊恐,凄惨哀呼:「可怕啊,可怕啊!上帝拯救我,怜悯我!主耶稣基督拯救我,怜悯我!」雷南(Renan)虽信基督,但却否认基督之神性,思想也流于悲观,尝谓「我的知识尽管增加,但是我对人类前途愈觉没有希望。」又如尼采(Nietzsche)迷信权力意志,斥基督教为奴才哲学,甚至以基督教的道德观,乃是一切虚伪之最恶劣的表现,乃是人间的妖魔,人类堕落的厉阶。尼氏不到三十岁,即神经失常,时患剧烈的头痛症;一八七九年(三十五岁)以后,便离群索居;其所著书,语多狂妄;神经变态,卒乃不治身死。凡此俱足为不信者之殷鉴!而今之哲人,尤当深思反省,知所悔悟。
第一,应当悔悟——「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林前一26-27)智慧人所以不蒙拣选,其一,乃是因为智慧人自作聪明,其实没有智慧;他们不能超脱窠臼,自拔庸俗,不能有超凡的境界,柏拉图没有智慧,因为他不能识透斯巴达制度的缺陷,乃反以之为其理想国之楷模。亚理斯多德没有智慧,因他不知奴隶制度之违反人性,而却为之辩护。古今中外一切哲学家,都没有智慧,因为他们都是以人为本,只是为人立言;不能打破自我的桎梏,脱离败坏的辖制,享受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罗八21)。其二,智慧人所以不被拣选,乃是因为他们既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救主。一方面,他们妄自尊大,予智自雄,自比神明;以为知识即权力,理知即真理。不知人虽能用其理知创造文化,却也能由其理知毁灭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妄自菲薄,以为在伟大的宇宙中,仅沧海之一栗。而不知基督教的精义,乃在主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奥秘的联合,及其与信徒之合而为一。人类一方面固是腐败堕落,为神所弃;一方面却又能因信称义,作神儿女。巴斯格(Pascal)说,这两个真理,乃是同样重要,不可顾此失彼。世上的智慧人、哲学家,往往知其一面不知其二,所以或则自以为神,妄想自建地上天国,不认识自己的败坏;或则不信有神,以为人类毫无盼望,而不知有救主。基督教的妙谛,乃在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林前一25);他「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太一一25)此则非「虚怀若谷」、「大智若愚」的人,不能了悟。
第二,应当悔悟——「上帝也拣选了……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林前一28)每一派哲学家,都抱其天真的幻想,例如黑格尔、孔德、马克思……都以为他们自己的道理,乃是绝对高明,至真至善。他们不但「文人相轻」,否定其他各家之言;而且还想与神斗智,以自己有限的理性,限制上帝无限的智慧与权能;结果,井蛙窥天,他们的理性变成了他自己狂傲的奴隶。更可怜的,哲学家明明存着天真的幻想,而却陷于幻想而不自知,以为只有他自己的学说,高人一筹,绝非幻想,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不惑;殊不知道这才是最大的幻想。上文所述爱因斯坦之言,他虽自叹其不能摆脱他自己理性的桎梏;但却终未悔悟,只有神的真理,才能使我们得自由(约八32)。人类的知识乃是有限的,「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林前一三8-12)。到了那完全的来到的时候,「那有的」便要被「废掉」,归于虚幻。我们当大彻大悟,丢弃「那有的」,完全倒空自己,成为那「无有」的,才能蒙神拣选,承受圣道,无有而无不有,在他的「真理」内得到释放;始能超脱陷阱,不作井蛙,而能见其大而窥其全。这乃是「正等觉」、真智慧、真哲学。
第三,应当悔悟——世俗学者,「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上帝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上帝的义了。」(罗一21-22,一○2-3)平心而论,世俗的哲学家,对于宗教和上帝的事,未尝没有「热心」。但是他们却不是「按着真知识」;他们乃在「椽木求鱼」,依靠自我的理性,反对权威的信仰。这乃是一种「理性的人文主义」。结果他们所求得的所谓「上帝」,并不是创造宇宙万物、自有永有、全智全能的上帝,而乃是「理性的上帝」(God of Reason),或是一种被造的「自然」(Nature)。这种哲理最能投合属血气的自然人,因为他们「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林前二14)。例如孔德,认为人类乃有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精神力量,可使人类社会团结一致、相亲相爱,此即所谓人道的宗教。又如杜威,更以为超自然的宗教,乃是社会文化进步发展最大的障碍,而各教派的道理,更使人类分成彼此敌视的阵营。所以他反对权威的信仰,而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以期泯除畛域,造成「共信」(Common Faith)。这些天真的想法,诚如保罗所说,虽是大有「热心」,但非「按着真知识」。他们妄想以人的理性来代替上帝,殊不知人的理性乃是各是其是,不可能有统一的内容,绝难形成共同的信仰。他们更不知人类乃是被造物,总不免其缺陷,他们的知识乃是「有限的」,不是「那完全的」,「终必归于无有」;而他们的义,也「像污秽的衣服」(赛六四6),「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五20);他们虽反对圣经权威的信仰,却造成自己的权威,反而变为一种自负自义、更趋偏激的狂热(Fanaticism);妄想「神化自我」,建立「地上天国」;否认真神,自造偶像;这乃是一种假的宗教,偶像崇拜;这不是「真知识」,乃是「假哲学」!